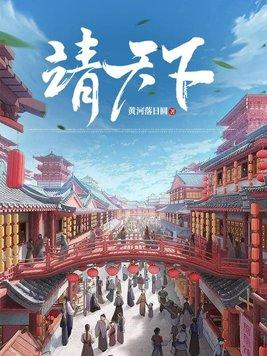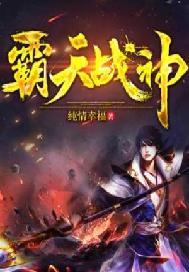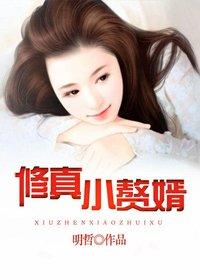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红楼之黛玉长嫂笔趣阁免费阅读 > 95第 95 章(第1页)
95第 95 章(第1页)
宝玉走后,黛玉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节奏。她每日清晨推窗看雪,午后泡茶读书,偶尔提笔写些随笔。日子虽平淡,却透着一种久违的安宁与满足。
这日午后,风和日丽,阳光透过稀疏的枝桠洒在院子里,照得石桌上的茶汤泛起微光。黛玉坐在廊下,翻着一本《庄子》,一边品茶,一边思索着书中的一段话:“梦中饮酒者,旦而哭泣;梦中哭泣者,旦而田猎。”她轻声念出,随即莞尔一笑。
“原来人生如梦,梦醒之后,方知悲喜皆是虚妄。”
她放下书,抬头望向远处的山林,心中忽然生出一丝莫名的惆怅。这种情绪来得突兀,却又似曾相识,仿佛是某种潜藏已久的思绪被唤醒。
她起身走进屋内,取出一叠稿纸,铺展在案头。她决定将这些年来的心绪整理成册,作为自己最后的作品??或许也是对过去的告别。
正提笔欲写,忽听得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她微微一怔,还未及反应,门已被推开,探春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几分焦急之色。
“颦儿!”她一进门便开口,“你听说了吗?江南那边出了事。”
黛玉眉头微蹙:“什么事?”
“那书院被人查封了,说是有人举报他们聚众讲学,图谋不轨。”探春语气急促,“我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但情况不容乐观。”
黛玉闻言,神色一凝:“是谁告的状?”
“还不清楚,但据说是朝中有人插手,背后恐怕牵涉不小。”探春顿了顿,低声道,“我担心你会受影响。”
黛玉沉默片刻,缓缓道:“我只是个文人,讲学、写作而已,并无他意。”
“可如今局势不同。”探春叹了口气,“你若继续留在这里,恐怕也会被牵连。”
黛玉低头看着案头的稿纸,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面,良久未语。
探春见她神情平静,忍不住问:“你打算怎么办?”
黛玉抬起头,目光坚定:“我想去一趟江南。”
探春大惊:“你现在去江南?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去。”黛玉缓缓道,“我不愿看到那些为理想奋斗的人因误会而受难。我也想亲自看看,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探春看着她,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你真的决定了?”
黛玉点头:“是的。”
探春沉吟片刻,终是叹息一声:“那我陪你去。”
“不必。”黛玉微笑,“你还有家要照顾,有责任在身。我去即可。”
“那你至少等我安排好一切,再启程。”探春坚持道。
黛玉没有拒绝,只是点了点头:“好。”
几日后,探春果然安排妥当,替她准备了一辆马车,并托付了几位可靠之人护送她南下。
临行前夜,黛玉独自坐在灯下,看着桌上那封宝玉的来信。她轻轻展开信纸,再次读了一遍:
“……我在南方开了一间书店,名为‘梦觉堂’。每日与书为伴,与志同道合者论道,心甚安。近日听闻江南之事,颇为不安。若你有意前往,请务必小心行事。若有需要,我随时可为你提供庇护。”
她将信折好,放入怀中,心中一片清明。
次日清晨,天还未亮,她便收拾妥当,披上大衣,走出小院。探春已在门口等候,身旁还站着几个护卫模样的男子。
“路上小心。”探春握住她的手,“到了江南,先找我安排的人,他们会带你去找书院负责人。”
黛玉点头:“我会的。”
她登上马车,回望一眼熟悉的小院,心中竟无半分留恋。
马车缓缓驶出京城,沿着官道一路向南。沿途风景变换,从北地的苍茫到江南的温婉,黛玉一路静静地看着窗外,心中却始终想着一个问题:这场旅途,究竟是为了什么?
十日后,她抵达江南。
书院已被查封,大门紧闭,门前冷清,只有几位老仆仍在守着这片废墟。
她找到探春安排的人,一位名叫沈先生的老者,对方将她带入书院后院的一间密室。
“林小姐,”沈先生低声说道,“书院确实遭人陷害,我们怀疑是朝中某位权臣指使的。”
“是谁?”黛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