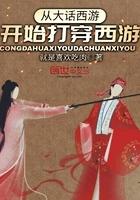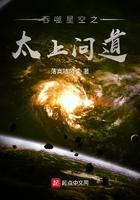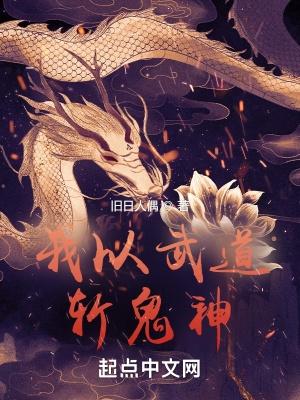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新浪微博坤颖姐弟 > 长沙一日约会(第1页)
长沙一日约会(第1页)
长沙的盛夏,阳光白得晃眼,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来。
工作日午后,街头的喧嚣也仿佛被这炽热蒸腾得稀薄了些。蔡徐坤站在一栋爬满绿藤的老建筑转角阴影里,鸭舌帽檐压得很低,鼻梁上架着一副细黑框眼镜——这倒不是为了伪装,他本就有些近视。
简单的白色棉麻衬衫,袖口随意挽至小臂,露出线条清晰的手腕,下身是条洗得有些发白的深色牛仔裤,整个人清爽得像一阵误入城市的风。
约定的时间刚到,另一个身影便轻盈地出现在街角。Baby同样低调,宽大的遮阳帽几乎盖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小巧的下巴和涂着裸色唇釉的嘴唇,高挺的鼻梁上架着大大的墨镜。淡粉色的吊带外罩一件薄如蝉翼的防晒开衫,行走间带起一个微凉的风。
她看见阴影里的蔡徐坤,脚步加快了些,藏在墨镜后面的双眼顿时眯了起来,像两弯新月。
“等很久了?”她走近,声音带着显而易见的轻快。
“刚到。”蔡徐坤嘴角自然上扬,镜片后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带着夏日阳光般的暖意。他自然地侧身,示意方向,“这边走,就在前面。”
他们的目的地,是藏在老城区深处一家名为“回声”的音乐书店。
推开厚重的、镶嵌着彩色玻璃的橡木门,一股混合着旧书页、干燥木料、以及若有似无的松节油的独特气息扑面而来,瞬间将门外的燥热与喧嚣隔绝。
书店冷气开得很足,让人毛孔都舒展开来。店内光线偏暗,只靠几盏暖黄色的壁灯和射灯照亮,营造出一种沉静的、与世隔绝的氛围。
墙壁几乎被顶天立地的深色木质书架占据,塞满了各种语言的音乐书籍。厚重的音乐史典籍、泛黄的乐谱、小众乐队的传记、艰深的乐理著作。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占据了书店中心位置和一面主墙的巨大黑胶唱片收藏区。成千上万张黑胶唱片被分门别类、整齐地码放在定制的格子里,从古典的巴赫、贝多芬,到爵士时代的MilesDavis、EllaFitzgerald,再到摇滚黄金时期的披头士、滚石,直至近年的独立乐队、电子乐先锋……时间在这里仿佛凝固,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声音被珍重地保存于此。
一台老式的、擦拭得锃亮的黑胶唱机静静地立在中央的胡桃木柜上,如同守护宝藏的卫士。
“哇……”Baby忍不住低声惊叹,摘下墨镜,露出一双清澈如小鹿般的眼睛,好奇地环顾四周,眼睛亮晶晶的,像发现了宝藏的孩子。“这里太棒了!”
“就知道你会喜欢。”蔡徐坤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他也摘下了帽子,露出一双深邃的眼眸。
他熟稔地走向爵士乐区域,修长的手指划过一排排唱片封套,最终停留在一张封面是抽象蓝调波纹的黑胶上。“ErikSatie的《Gymnopédies》,”他抽出来,递给Baby,“他的曲子很空灵,像漂浮的羽毛,又带着点淡淡的忧郁。感觉……你会喜欢。”
Baby接过唱片,指尖拂过封面上细腻的纹理。蔡徐坤的形容精准地击中了她对某些音乐的偏好——那种不激烈、却直抵心灵深处的力量。她抬头看他,眼底是真实的惊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调调?”
蔡徐坤只是笑了笑,没回答。他示意她跟着,走到那台老唱机旁。
店主是一位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老先生,看到蔡徐坤,微笑着点点头,一副认识他的模样。
蔡徐坤将唱片递过去,低声说了几句。老先生接过,动作轻柔而专业地将唱片取出,放置在唱盘上,调整唱针。
片刻后,空灵、纯净、带着一丝疏离感的钢琴旋律,如同清冽的山泉,从优质的复古音响中流淌出来,瞬间充盈了整个静谧的空间。
是萨蒂的《luo体歌舞》第一号。音符简单,重复,却营造出一种近乎禅意的平静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带着距离感的温柔忧伤。
Baby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任由那清澈又带着冷感的旋律包裹自己。蔡徐坤没有打扰她,只是安静地靠在旁边的唱片架上,目光专注地落在她沉浸的侧脸上。
暖黄的灯光勾勒着她精致的下颌线和微微颤动的睫毛。这一刻,时间仿佛被拉长,凝固在这方被旧书和古老音符守护的天地里。空气中只有流淌的钢琴声和他们之间无声流淌的默契。
一曲终了,Baby缓缓睁开眼,对上蔡徐坤温柔凝视的目光,脸颊微微泛红。“真好听,”她轻声说,“有种……时间停驻的感觉。”
“嗯,”蔡徐坤点头,“这里就有这种魔力。”他指了指书店角落一个不起眼的小木桌,“看到那个了吗?老板说,这里可以给未来的自己寄信。”
小木桌上摆放着复古的铜制蘸水笔、各色火漆印章、精致的信纸信封,还有一个小巧的、标注着不同年份的邮筒模型。
“寄给未来?”Baby来了兴趣,走过去拿起一张散发着淡淡木香的米白色信纸。
“对,时间跨度可以自己选,一年、三年、五年……写好封好,老板会帮忙保管,到了时间再寄出。”蔡徐坤也拿起一张信纸,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纸面,眼神里闪过一抹复杂的光芒,像是期待,又像是某种隐秘的决心。
“不如,我们写给对方吧?”Baby率先打破两人之间微妙的气氛,俏皮的眨了眨眼睛。将手中的信纸摊开。
“嗯!”蔡徐坤也是这么想的。
两人默契地没有交谈,各自拿起笔,背对着对方,在信纸上书写起来。书店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角落里黑胶唱机偶尔传来的细微运转声。
蔡徐坤写得很快,却又时不时停顿,笔尖悬在空中,仿佛在斟酌着笔下的的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