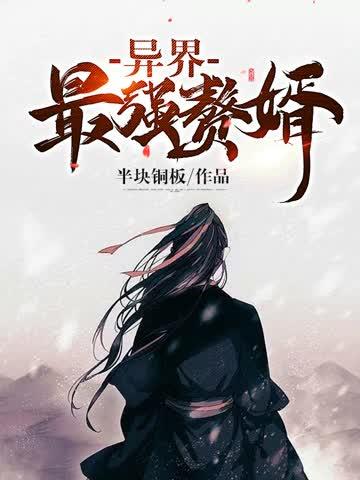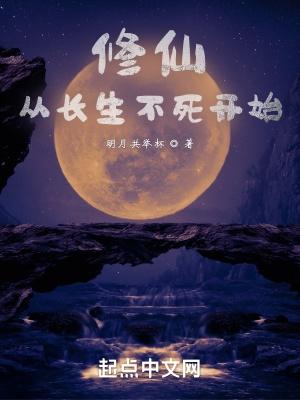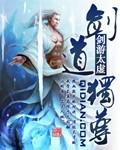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当世界变成一片黑暗 > 第一百章 曲终下(第2页)
第一百章 曲终下(第2页)
除此之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也成了陵山国的沉疴固疾。
在连启平的领导下,陵山国的商业变的格外发达,然而,发达的可能也就剩下商业了。
工业、农业、教育、医疗、文化、军事等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严重退化。
没有了“自主创新”作为源头活水,陵山国的工业水平变得相当迟滞落后,企业家们宁可多建几座“国际商贸中转站”,也不愿修建一座工厂,他们总习惯于“从实际出发“把精力和金钱投入到能给自己榨取更多利润,博得更大名声的地方。
教育和文化更是落后至极,随着私有化制度的高速发展,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又回到了蒋经纬时期的两极分化状态。
公办学校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什么有用的知识,他们的父母没钱供他们去上更好的学校,他们也活该当一辈子的穷人。
早期的民办学校,还能算是个培养精英的好地方,后来,它们也逐渐变成了公子小姐们挥霍时间和金钱的“游乐场”,风气比从前的苍梧中学还要乱上几倍,彻底失去了自己作为一所学校的意义。
以至于到了连启平执政后期,陵山国的教育水平竟然连永绪国这个仍然实行封建制度的国家都比不上。
现在的“文艺工作者”们已经不能再称之为文艺工作者了,他们出卖掉了自己的良知和尊严,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连启平和其他“上流阶层人士”的小跟班。
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不是阿谀奉承的歌颂与赞美,就是风花雪月的浪漫和爱情,总之就是一点营养都没有。
至于那些真正有内涵有思想,具有现实批判意义和针砭时弊作用的优秀作品,早已被连启平以”不利于团结稳定”的名义予以禁止,彻底淡出了人民群众的视野。
人们却依然在沾沾自喜着,以为自己告别了过去单一、枯躁、死板的旧文化,迎来了现在丰富多元的新文化。
谁知道,他们自以为是的“文明绿洲”,实质上就是一片根本汲取不出半点养分的文化荒漠呢?
陵山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弱到了一种令人忧惧的程度,大量本应该投入到国防建设和军备开支上的经费都被挪用到商业领域。
按照“新真理主义”的理论,商业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心,其他的领域,哪怕关乎国家安全和民生疾苦,也不值得去投入大多金钱和精力。
这一显然偏颇荒唐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将陵山国变成一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外表光鲜亮丽,里面却全都是空的,遇到侵略者的时候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连启平就这样一直春风得意了很多年,往后的每一天,对于她来说似乎并没有太多不同。
每年的5月15日,她都会带着一些糕点和酒水,到那片位于荒郊野外的孤坟去祭奠江衡,向她诉说着自己的苦衷。
她不愿悔改,也永远不会悔改,一生都在给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1894年,赵思贤刑满释放。
目睹着“自由世界”里这幅物是人非的景象,他感到惆怅不已,认为陵山国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了。
万般无奈之下,他向总统连启平请求从这个国家离开,连启平巴不得他滚出自己的管辖范围,给了他离开陵山国的权利。
后来,他漂洋过海到了永绪国,在首都的一所小学当了老师,他总是相当的勤奋热情,在学校里面人缘相当的好,就连校长的女儿,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数学老师都对他产生了好感。
他们没过多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又很快的就结了婚。
婚后,赵思贤因为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比不上妻子,只好依照着永绪国的习俗把自己的姓氏改掉,改成和自己的妻子一样,从此得名静嘉思贤。
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叫作静嘉天楚。
这个静嘉天楚长大后没什么出息,他的两个女儿却都成为了一代名流,一个成了永绪国将来的第一夫人,一个成为了永绪国的宣传部长,共同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兴起与覆亡,这是后话。
1899年,王存真重获自由。
一向斗志昂扬的他也被岁月磨平了棱角,有了几分看破红尘的意味,他不愿再去追逐那些海市蜃楼般虚幻的繁华,而是选择彻底告别世俗的喧嚣,和自己的妻儿一起留在教会中修行,过着平淡却幸福的生活。
偶尔,他也会梦到从前那个充满斗争热情的峥嵘岁月,梦到从前和自己并肩作战的那些好同志,梦到他最为敬爱的领袖李昭旭,醒来后,泪水已经打湿了枕席。
“唉,那个美好的时代,它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
王存真在教会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直到1932年溘然长逝,享年69岁。
江绫在1910年徐素英逝世之后接替她成为教长,在1934年去世,享年73岁。
高宇峥终究没能等到重获自由的那一天,他在1902年就因病逝世,年仅49岁。
他曾经的妻子陈雪早已嫁给了一位商人,后半辈子都衣食无忧。
后来“张尚文集团”已经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关于他们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些胡编乱造的“纪实文学”或是相当主旋律的批判类作品,都已经在连启平执政后期被列为禁书,不许再出版,销售,阅读了。
“铭记历史并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只要活在当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