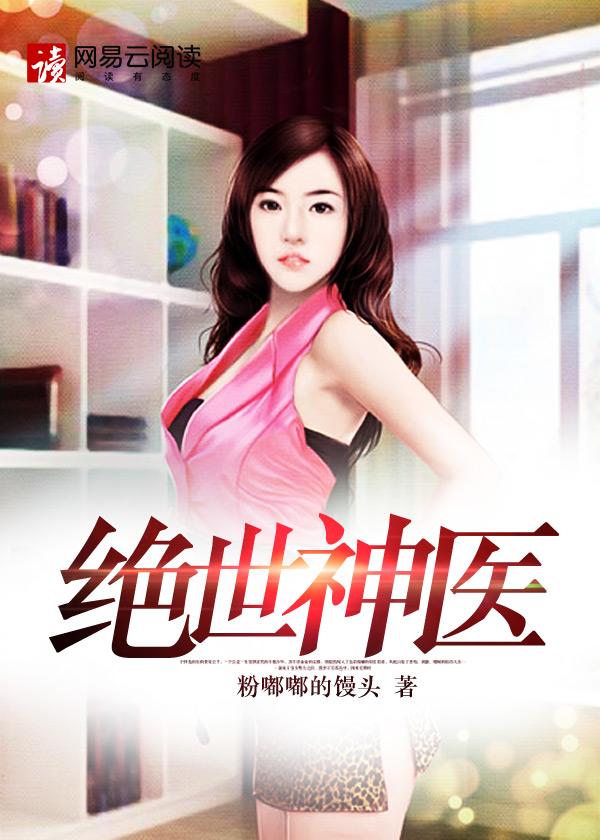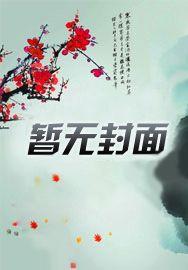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强娶男主他替身[穿书 > 她偏要争(第1页)
她偏要争(第1页)
秋意渐深,帝京铅云低垂。
东宫书房内,太子宁晏清眉宇间积着化不开的凝重,案头奏疏堆积如山,监国的担子远比他想象的更沉,太子詹事陈大人侍立一旁奏对,花白的眉峰亦微微蹙起。
殿门轻启,雍王步履从容地走了进来。
“皇兄辛劳。”声音温和,目光扫过太子案头,最终落在那份关于明州减税的奏报上,“明明珠妹妹这动静,着实不小,百姓自然是欢天喜地,颂声载道了。”
“明珠妹妹终究是女儿家,她这般大张旗鼓,恐非社稷之福,也易授人以柄啊
太子搁下朱笔,抬眼看他,眼神平静无波:“明珠心系封地子民,自减其封邑税赋,于情于理,并无逾矩之处。”
雍王微微颔首,唇边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浅笑:“皇兄说的是。明珠妹妹一片仁心,臣弟自然明白。只是此例一开,其他州府如何自处?若各地百姓若要求效仿明州,朝廷是准还是不准?”
他皱着眉,似乎有难处。
“准了,国库空虚,如何支撑?不准,岂非显得朝廷厚此薄彼,皇兄正值监国,您这仁厚之名,又置于何地?”
太子捏着笔管的手指微微收紧,他当然听得出这话里的挑拨。
“晏礼多虑了。”太子声音依旧平稳,“明珠时有灾情,减税赈灾亦是常理。赋税增减,关乎国本,岂能因一地之善政而攀比妄动?户部自有章程,孤也自有考量。”
雍王面上却显出被点醒般的恍然:“是臣弟思虑不周了。皇兄高瞻远瞩,臣弟佩服。”
他顿了顿,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只是不仅减税之事,更将那探花郎沈清砚,一举擢为代别驾。这沈探花,入仕才几日?朝廷上下哪一个不是熬资历拼门第?他一个寒门子弟,骤然登此高位,难服众啊。臣弟偶闻有士子言朝廷科举不公呢。”
最后一句,他声音放得极轻,却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荡起了层层涟漪。
太子端起手边的茶盏,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眼底瞬间闪过的复杂情绪。
“够了。”太子放下茶盏,“沈清砚是父皇亲口允准,拨给明珠开府建牙所用之人,其才干如何,明珠自有判断。朝廷如今要务在北境粮运与京畿安稳,无谓在这些枝节上纠缠。”
他目光锐利地看向雍王,“若无切实关乎国计民生之要事,晏礼,你且退下吧。”
“臣弟遵命。”雍王躬身行礼,姿态恭谨,“皇兄为国事操劳,也请务必保重贵体。”
转身退出御书房时,他垂下的眼帘遮住了眸底深处的满意。
殿门合拢,沉重的寂静重新笼罩。
一直沉默如石的陈大人这才上前一步:“殿下,雍王殿下今日之言,句句不离明珠公主,其意在离间,更在搅动浑水。公主于大局,实无大碍。”
见太子脸色不变,他继续说道:“皇上明您监国理政,此刻若因猜忌乱了阵脚,非但落人口实,正中雍王下怀。当务之急,仍是稳字当头,静待陛下圣体康安。至于公主处……”
他顿了顿,“多加留意即可,切莫轻动,以免打草惊蛇,反生枝节,待以后。。。。。。”
太子沉默良久,目光落在案头那份关于北朔粮草押运的紧急奏报上,明珠牵涉北朔,若北朔动,则南朝乱,这监国的差事更难办了。
他疲惫地闭了闭眼,再睁开时,已敛去了所有情绪:“陈卿老成谋国,所言极是。孤知道了。”
他拿起那份北境急报,指尖却在不经意间,重重按在了奏报边缘明州之上。
雍王走出东宫书房,脸上那点伪装的轻松彻底消失。
他穿过幽深的甬道,对身后内侍低语:“去,安排人,把该说的话,传到明州去。要快,要遍地开花。”
他不信,不信太子能容忍他人染指权柄,收拢人心,即便这个人是公主,太子也绝不会坐视不管。
皇兄啊,皇兄,这监国的滋味真的好受吗?难道不想更进一步吗?如果你不想,那我就帮你一把。
此刻,千里之外的明州,笼罩在无边无际的秋雨之中。
新任代别驾沈清砚的政令,甫一推行,便猛烈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