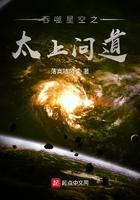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荣婚重生17章 > 第240章(第1页)
第240章(第1页)
她在院子里歇了一日。
第二日还在下雪,她窝在被褥里更不想起来。
眼巴巴盼着第三日的?到来。
这一日天可怜见放了晴。
嬷嬷过来照顾她起居时,多了一句嘴,
“今日家主出了门,说是庄田那边出了事,要去看一看。”
她心里就有些失落,不会爽约吧。
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午后,她忽然?吐得昏天暗地,只当自?己着了凉,喝了几口热水温在被褥里,到底是惊动婆母,婆母是稳妥人物,带着府上?的?大夫来了。
她看着大夫,忽然?一愣。
再然?后,大夫给她搭脉,她只听见喜脉二字,脑子里一片浆糊。
老太太喜极而泣,抱着她哭天抢地,
“好?孩子,咱们总算是怀上?了,总算是怀上?了,你?不必再受罪了”
不必再受罪了
夏芙怔愣当场。
直到今日她都无法形容那一刻的?心情?。
她被老太太搂在怀里,磕在她消瘦的?肩骨,迟迟笑了笑,“是喜事。”
一夜北风吹。
她坐在琴案望着月洞门口,被雪压弯的竹条堵死了他来时的路,从约定好?的?戌时一直坐到亥时,膝盖都麻了,一贯伺候她的那位老嬷嬷心疼地抱着毯子裹在她身上?,将她拥在怀里,
“不必等了,家主不会来了。”
滚烫的?泪珠砸在琴案,碎成水花。
“只待你?怀孕,我们不再相见。”
“好?,有了身子,我?一定不再叨扰家主。”
十?九年过去了。
熟悉又陌生的?旋律,跟蚕丝一样一点点往她四肢五骸钻,往她心上?缠。
夏芙深深闭上?了眼。
台上?的?程明昱已试过音。
长公主听闻他要弹琴,已转过身子面朝琴台的?方向。
抛开她对这个男人的?情?愫,程明昱是音律大家,他当众抚琴,便是一场视听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