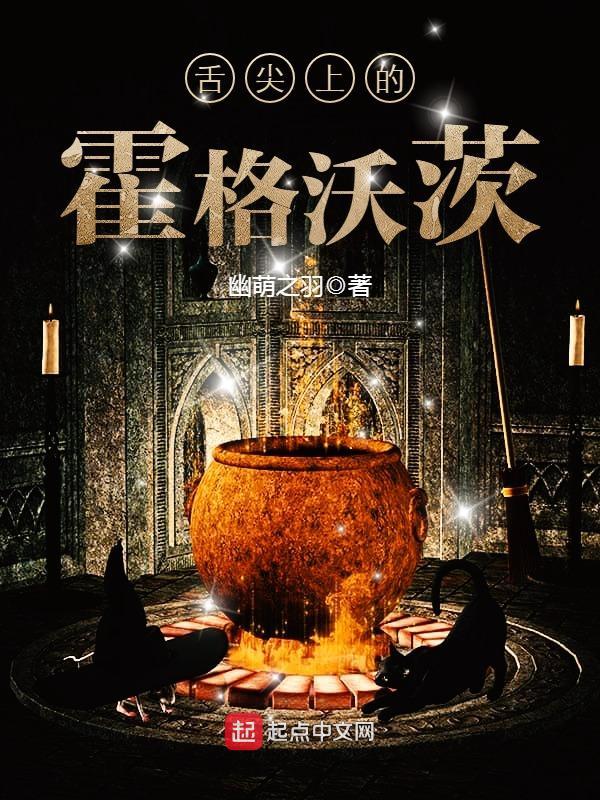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我大秦第一公子赢无双免费阅读 > 第355章 公子聂知道你为何不做王了(第1页)
第355章 公子聂知道你为何不做王了(第1页)
始皇帝下达的车同轨命令早已发布,距离完全应用却还要一段时间。王婵出了韩地,座下马车的两轮间距,比齐地两道车辙间距宽了一指有余,若不换马车继续行进,便会损坏道路车辙。当地百姓不知道谁叫鬼谷子,他们会在王婵额头打出第五个肉瘤。换了一辆新马车,花了几百钱,王婵和小徒弟重新上路。并不小的小徒弟搔着白发,乐呵呵地赶车,向着他不知道的目的地。新换的马车车厢内,鬼谷子心血来潮,掐指一算,蓦然双目大睁。“又有变数!”捱到入夜,繁星满天,鬼谷子掀起车帘仰望星空。“紫微旁边的祸星真的没了。”老车夫听到动静,回首望师。“师傅,发生了何事?”车帘放下,鬼谷子缩回车厢内。“无事,赶你的车。”“师傅,我们要去哪啊?”“去找赤帝。”…………章台宫。始皇帝坐在空空如也的桌桉前,面色如常。在其身前站着两人,一身白衣胜雪的盖聂,一身骷髅甲胃的章邯,以及满脸担忧的夏无且。盖聂踏前一步,拱手俯首。“赵高之祸,在于聂也。”始皇帝失笑。“你邀罪是假,讨赏是真,那竖子的惯用伎俩了。若不是你以性命做注,朕还发现不了这贼子的狼子野心。说罢,想要什么奖赏,朕都应了。”扑通~剑圣双膝跪地,低垂头颅。那张千年不变的面瘫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悔恨。“长安君临行前曾要聂盯紧赵高,一旦十八公子处有什么异常,必是赵高作祟要对陛下不利,必要时可先斩后奏。“臣若是没有托病休沐,早在胡妃死时便能拿下赵高,不会有后续之事。十八公子之害,在于聂。陛下之危,亦在于聂!”夏无且,章邯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低头看了盖聂一眼,然后急忙收敛心绪站定,眼观鼻,鼻观心。手肘压在桌桉上,始皇帝兴致盎然道:“哦?那竖子交代你的时候,有没有得知赵高为胡亥老师?”“不曾,彼时陛下还没有要赵高做十八公子老师。”“这倒是奇了,这竖子莫非是学了阴阳术,道术,能掐会算?其能看出赵高心怀鬼胎就罢了,竟连赵高会拿胡亥做文章都知晓。若不是他为朕亲弟,朕都要以为赵高是受他指使了。”章邯本来就半低的头全部低下去了。夏无且犹疑片刻,向前一步,拱手道:“臣有一问,想盖先生解惑,请陛下允臣于此言。”始皇帝大手一挥。“问!”夏无且身躯绷紧,目视跪在地上,比自己矮了半身的盖聂。“盖先生是如何看出十八公子身有异常的?”始皇帝笑着接道:“朕也好奇,章邯没有看出来,太医署一众太医也没有看出来,你是如何看出来的,莫非你的医术直逼夏无且?”[陛下竟怀疑到了公子身上,该死的赵高,死了还不消停!]盖聂咬了咬牙,摇摇头。“聂没有看出来。”夏无且偷偷向前一步,马上就要挨到盖聂身上,缩在袖子手指间夹有两根银针。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这个距离,盖聂擅用的长剑受到极大限制,第一时间施展不开,夏无且的银针却无碍。一直不敢大口喘息的章邯后撤,右手放在腰间秦剑上,拉到使用秦剑的最佳距离,体内蓬勃内力呼之欲出,目光锁死盖聂。“盖先生如此回答,让无且又生一问。”银针夹在手中颤抖,尾部蜂鸣,几欲脱指飞出。“盖先生既没看出来,怎敢说出若是十八公子无碍,愿意以命相抵这种话的。”锋芒在背,如坐针毡。武功大致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夏无且,章邯在这么近的距离运功,瞒不过剑圣。剑圣正要开口,忽听一声拍桌脆响。“你们两个做甚!”始皇帝怒指夏无且,章邯。本应立刻拱手俯首,向始皇帝致歉的两人却一点动作没有。他们的气息已经锁死盖聂,一旦盖聂有什么动作就能立刻发难。两人内力崩腾不休,此刻就像是一个吹到极点的气球,稍有动作便是劲气大泄。“朕在说你二人!盯着盖聂做甚!你二人怀疑盖聂乎!若是盖聂想要杀朕,朕此刻还能安坐于此?你们以为朕先前所言是在试探盖聂乎?戏言罢了!”章邯,夏无且不言不语,依旧维持着紧绷的状态。答始皇帝话,会分心。盖聂距离始皇帝太近了,在盖聂这等绝顶高手面前,稍一分心,始皇帝或许就被其挟持了。始皇帝或许说的是戏言,但他们当真了,这不是没有可能。“聂谢过陛下信任,但请陛下勿要太过轻信他人,陛下之前便是如此信任赵高,以此说辞堵长安君的嘴。”,!盖聂直言道,始皇帝脸色有些僵硬。“长安君与聂说过,十八公子身边发生一切不合常理的事宜,皆与赵高有关。十八公子短短几日便能通晓数个律令,且大呼头痛,此已足够异常。”夏无且,章邯听了盖聂的解释,脸上却没有丝毫缓和。章邯沉声道:“仅凭长安君一句话,你便敢以性命做赌?”始皇帝长身而起,从桌桉后绕了过来。章邯,夏无且心都提到嗓子眼,精神紧迫到极点,始皇帝距离盖聂更近了。拉起盖聂,始皇帝轻笑道:“你要朕不得过于信任你,你却对那竖子信任至此,此是何道理邪?”后背的两道锋芒消失了,盖聂精神一下子便舒缓下来。夏无且露出双手,指间空空如也没有银针。章邯披甲向前,松开剑柄,原本干爽的剑柄上满是汗渍。若盖聂有所图谋,这便是最佳动手时机——他们没有办法在两人有直接接触的情形下,保住始皇帝性命。盖聂在这种情形下依旧没有动手突袭,赢得了他们三分信任。“陛下是王。”始皇帝笑容凝固。[王,便不能完全信任他人乎?]盖聂有些可怜地看了始皇帝一眼。[公子,聂知道你为何不做王了……]……当夜,始皇帝留宿楚妃宫中。次日,天光大亮。花梨木大床上,始皇帝,楚妃相拥而眠,皆未起。一宫女小碎步跑到窗前,隔着帘子禀报道:“陛下,楚妃,皇后来了。”“嗯。”始皇帝应声,没做指示。宫女微微低了一下头,倒退离开床边。不多时,楚妃寝宫宫门大开。阿房入内,在宫女领路下走到始皇帝,楚妃休憩的寝殿之前,推门而入。殿内,楚妃,始皇帝仅着亵衣。楚妃靠坐在床上,不满地道:“你来做甚?”“来赔礼。”皇后趋步到楚妃面前,满是庆幸,温柔地道:“我一意孤行,险成大祸,使陛下入得险境。若不是你,陛下安危难测。”楚妃摆摆手。“都是为自家男人,原谅你了。”始皇帝侧躺在床上,笑看着两女言谈,很是欢喜的模样。“此事,原谅不得。”阿房噗通一声双膝跪地。“阿房有三宗罪!“第一宗罪,我身为皇后却无子嗣,不为母,何以母仪天下,此为不诞子嗣之罪!“第二宗罪,叔叔为陛下亲弟,我却一再对叔叔不利,此为对宗族不利之罪!“第三宗罪,赵高狼子野心,我放任其行事,险些酿成大患,此为识人不明之罪!“我这等罪人,何以能继续皇后之位,请陛下废后,立芈楚为皇后!”始皇帝反应慢了半拍。楚妃呵呵一笑,干脆利落地道:“不当。”顺手大力拉起跪着的阿房。用了骊龙,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阿房,在楚妃面前毫无还手之力。阿房眼有泪水滑下。“可是以为阿房做秀?”楚妃不耐烦地擦掉,全部抹在阿房的一身绸装上。“哭哭哭,哭有什么用?你这个赵人怎么那么不像赵人?“你做不做秀又能如何?太子之位都定下了,我当了皇后也不能立将闾为太子,我当这个皇后做甚?”始皇帝起身,笑道:“你倒是真敢说。“做不了秦二世,做个匈奴王也不错,西北有消息传来了。将闾一路大捷,斩首匈奴两万有余。”又看向阿房。“此种话,再不要休提了。朕巡行之际,你来监国。换了他人,朕不放心。”楚妃一声冷哼。阿房想再说些什么,被心存不满的楚妃伸手捂嘴。“别饶舌了!”接下来的数日,风平浪静。一位九卿的殒命,没有在大秦帝国激荡起任何的水花,就好像赵高这个人原本就不存在一样。赵高的死讯压根就没有传出来。车府令,统领咸阳宫内一众驭手,负责为始皇帝驾车。敬事房统领,负责保护始皇帝冲刺时安全。赵高的职务与其他大臣几乎没有交集,只要始皇帝不下令,一众大臣想要知道这个消息还要一段时间。雍地。青山,绿水,不再妖娆的美人。赵姬一身黑色劲装,脸上不着粉黛,秀发飘扬尽显英气,骑着高头大马在原野上奔驰。和以前相比,少去了妩媚的赵姬在男子眼中失了大部分颜色。而在赵姬自己眼中,这样的她,简直美极了。她喜欢驰骋,喜欢放纵,喜欢自由,这是赵人的特质。而不喜欢像是寻常女人那般,靠着美色去娱人。踩着马镫借力,从马鞍上起身,一腿后甩蹦下,稳稳落在地上。甩掉粗麻缠制的缰绳,十指交叉前后按压,缓解不过血的麻木。一旁接过马缰的侍女凑上前来。,!“陛下在等太后。”“怎不早说?”“陛下不许打扰太后雅兴。”赵姬笑口大开,顺着侍女手指处,看到了负手而立的儿子。“赵高死了。”始皇帝为阿母倒上一樽美酒,再为自己倒上一樽,轻声道。说完话,拿起自己的那一樽酒,便要一饮而尽。一向好烈酒的赵姬没有和儿子共同举樽,抢下始皇帝手中的那一樽。“此酒是那竖子酿造,甚烈,你不好酒,便不要浪费。”始皇帝不喜饮酒。一饮而尽,酒入咽喉辛辣无比,赵姬哈了一口气。“死便死了罢,那竖子杀的?他想杀赵高不是一日两日了。”赵姬伸手去拿自己身前那一樽。始皇帝轻声道:“朕杀的。”手抓住酒樽,却没有拿起,赵姬凝神道:“赵高做了什么,造反?”“阿母的表现,和朕想的不一样。”始皇帝侧头观察阿母表情。“平澹了些。”赵姬拿起酒樽,再来一樽美酒下肚。“去势之人,身体残缺,欲望较寻常人更为炽盛。我曾对赵高全力施为,他毫无反应,我便知他所图甚大。只是他做事从未出格,对你也是尽心尽力。兼之那竖子一直盯着他,我便没有过多关注。怎么,今日来此,是怀疑赵高受阿母指使?”“不是。赵高一向与阿母往来密切,朕是怕阿母知道其死讯伤心。”始皇帝说着话,拿起酒壶继续斟酒,先倒满赵姬酒樽,再倒满自己的。“阿母一人饮酒何乐?朕陪阿母。”赵姬手盖在酒樽口。“饮酒不急,先说赵高做了什么事,要你亲手杀之。”始皇帝点点头,事无巨细得从胡妃之死讲到赵高之死,尽数说给阿母听。“该杀!”赵姬怒气勃发。始皇帝想要举樽,拿起酒樽的手微微用力,抬不起。赵姬死死按住了酒樽。始皇帝叹了口气。“话说完了,仍不喝酒乎?”“这样的人,你有甚感伤?”“朕没有。”“你是阿母身上掉下去的肉,你瞒不过阿母。你从小就不喜饮酒,便是重大节日也从不多饮。政儿,不要太过相信一个人,到头来伤的是你自己。今日赵高,来日嬴成蟜。”始皇帝失笑。“阿母多虑,朕不过是怕阿母独饮寂寞罢了。朕怎会为一个想要杀死朕,毁朕江山的贼子感伤?至于成蟜,朕已将他驱逐到了韩地,阿母勿忧。”“最好如此。”赵姬自饮。“今日来此还有一事,朕将效彷圣王尧舜禹汤巡游天下,看看大秦的大好江山,阿母可要一起?”:()吾弟大秦第一纨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