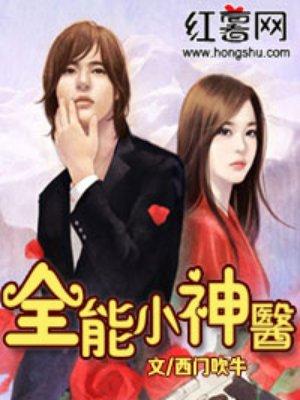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娇宠帝媳全文免费阅读 > 第 63 章(第1页)
第 63 章(第1页)
铅云压城,天光凝滞如铁。
寿康宫,这座曾煊赫两朝的太后寝宫,雕梁画栋间香烟缭绕四十载,而今已然朱漆剥落,唯有庆宁公主大婚的喜幡在檐下交错,掩盖下廊间的积灰。
正殿像口冰窖,未燃的炭盆在角落泛着冷光。
正殿中央,一张茶案,庆宁端坐。
婚服金线在幽暗中明明灭灭,宛如困在蛛网里的凤蝶。
殿内空荡荡的,伺候的人都被庆宁赶走,寂静得仿佛能听见烛火燃烧时轻微的“嗤嗤”声。
顾矜站在离庆宁十步远的地方,看着眼前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公主。
一个月未见,庆宁瘦了许多,原本丰润的面容此刻清减得有些陌生,只有那双肖似萧临川的凤眼依旧倔强地透着几分骄纵,仿佛在用这最后的矜持支撑着自己的尊严。
庆宁抬眼看向她,唇角微微勾起,语气冰冷:“令妃如此小心,站那么远做什么?”
顾矜唇角微扬,露出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
她迈着从容的步子走近,在庆宁面前的蒲团上优雅落座。
庆宁执起青花瓷壶,为顾矜斟了一杯茶。茶水落入杯中,发出漱漱的声响。
"请用。"
顾矜看了眼茶盏中的水纹,毫不迟疑地端起,轻抿一口。
"令妃好胆色,不怕我下毒?"
顾矜放下茶盏,语气平静如常:"现在下毒,公主若有什么筹谋,便功亏一篑。"
“筹谋?”庆宁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像是嘲讽,又像是自嘲,“本宫一个阶下囚,还能有什么筹谋?”
顾矜道:“公主并非真心想嫁给沈钰。”
“呵,连你都看不上的登徒子,本宫会甘心嫁给他?”庆宁嗤笑一声,语气里却透着一股难言的苦涩。
顾矜凝视着庆宁,嗓音温柔却暗含深意:"今日这一袭嫁衣,是公主光明正大走出寿康宫的敲门砖。"
她顿了顿,指尖轻轻拂过庆宁衣袖上流转的金线,"至于日后——这嫁衣是要恭恭敬敬地供进沈家宗祠,还是裹着行囊远赴关外,抑或。。。。。。"
她的声音渐低,"绞碎了投进护城河,那便都是公主的自由了。"
这句话仿佛戳中了庆宁的心事,她瞳孔骤缩:"你说什么?"
顾矜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敛眉又看向了杯内的水纹。
庆宁,这个从小娇纵跋扈、满心依恋萧临川的公主,真的只是个一无是处的蠢货吗?
太后掌控后宫权柄数十年,庆宁在她膝下长大,耳濡目染,怎么可能是个胸无城府的白痴?只是,她过惯了被太后和萧临川捧在手心的日子,所有东西唾手可得,她自然觉得全天下的东西,都该由着自己拣选。
这样的人,又怎会甘心被人摆布命运?
自从目睹白芷吞金的那一幕,顾矜便察觉到了异常。这方世界中的每一个所谓NPC,恐怕都已觉醒,都有了自己的意识。
按照剧本,庆宁应该会在大婚当天决绝赴死,以此成全她对萧临川的痴狂与忠贞。
但现在的庆宁,真的还是那个剧本里的庆宁吗?
顾矜心中浮起一丝冷笑。王朝最尊贵的公主,若已经觉醒,又怎会甘心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不过以己度人,"顾矜抬眼,目光清澈见底,"只要风风光光地将公主送出寿康宫,至于后来发生什么,那便不是我该管的事了。"
庆宁冷哼一声,盯着眼前的茶烟:"本宫竟看走了眼,原以为你不过是个靠着狐媚手段攀龙附凤的蠢物。这一次,到底是我输了。"
顾矜执壶斟茶的手稳如静潭,碧色茶汤在青瓷盏中旋出细小的涡流:"殿下说笑了,哪来的什么输赢。"
"君恩如三月檐上雪,看着皎洁,日头一照便化了——您自幼长在宫闱,竟还信这吃人不吐骨头的九重天阙里,能养出什么真心?"
"哈哈!"
庆宁一怔,忽然低笑出声,染着丹蔻的指尖轻轻点着案上水渍:"你这是什么意思?话里话外的,莫非你和表哥这些时日的君恩深重,也只是在演戏?"
顾矜垂眸望着被庆宁抹开的水渍,许久,她忽然也轻笑一声:"情真如何,情假又如何?"
"这宫里最不值钱的便是真心,不过和这水一样,泼出去,总归会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