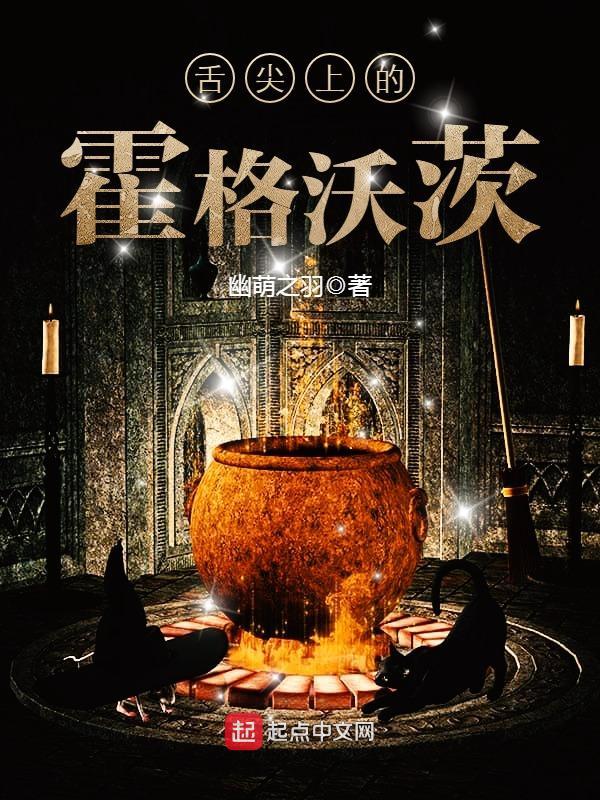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妈妈死了我很伤心 > 第306章 她在洗澡(第1页)
第306章 她在洗澡(第1页)
翌日,薛知恩被齐宿叫醒。“我帮你把行李收拾好了,里面的东西你到了那边都用得上,你起来看看还缺什么。”冬季昼短夜长,窗外灰暗房间点着盏床头灯,薛知恩醒的迷糊,本能地在他温暖的手掌里蹭了蹭。“我还想再睡会儿。”齐宿微滞的指尖轻摸她的面颊:“可以啊。”“……”似乎是意识到什么,薛知恩骤的睁开眼,跟他眷恋的神情撞了个正着,她猛地脱离他的掌心掀开被子下床。齐宿还保持着弯腰的姿势,沉默地看着她匆匆离开的背影,许久,他把被她依赖过的手放在鼻尖,郁沉的眸染上陶醉,辗转摩挲。没关系的。他可以等。“我送你。”齐宿拉起她的行李箱。“助理已经到楼下了。”他坚持:“让她跟着我的车。”“没必要这么麻烦。”薛知恩抢过自己的行李箱上了电梯,她还是不看他,余光里只有他大衣沉闷的衣角。同样的衣角她在候机厅也看到了,这种感觉就像男鬼缠身,让人后背发凉,好在男鬼并没有跟她上飞机。“薛总您在找谁吗?”“没有。”薛知恩敛下四处张望视线。“您不是说这次选开线上会议吗?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助理感觉奇怪,“是跟齐先生吵架了?”“没有。”薛知恩再次否定。他们几乎是吵不起来的,他会包容她一切情绪。这想法落地,薛知恩抱住了脑袋。她要呼吸不过来了。她试图挣扎一下。“如果我要跟他分……”‘开’字未吐出来,她就想到一句话——弃养不是人。齐宿从机场回来,照样备菜准备午餐,泛着寒光的刀刃切着鲜红的肉块,他随着耳机的音乐轻晃围裙,一条消息提示音让他分了神,如果有人细心会发现,上方播放的并不是什么音乐而是录音。他抬头看去不是想看到的那个人。‘咔。’指尖的疼痛唤回他的神智。齐宿看着案板上滴滴答答的血,安慰自己,她还在飞机上到了就会给我发消息。但等他把手指包扎好,午饭做完了,手机还是安静如初。zn:【你下飞机了吗?】已经坐在酒店餐厅的薛知恩收到这条消息。她把手机反扣。她还要再想想。齐宿想她应该是在忙。他等。就这么从太阳当空等到日落西山,手机像死了一样。他反复看电量,看信号,都没有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齐宿去照全身镜,他开始自省,薛知恩不是个喜新厌旧的人,她很好,那就是他不好。他看自己的脸、头发、皮肤、骨骼。是他变丑了吗?是他太烦人了吗?是他……他找不到答案。薛知恩突然无视他的第二十四个小时。齐宿感觉他可能会疯。第二天。他照常做饭作画,薛知恩在早上回了他一条。【到了。】他盯着那两个字,想把它们吞进肚子里保存。第三天。她给她发了张会议桌照片,她坐在中间神情认真,很严肃庄重的照片。齐宿看着捞过快被磨破的她的贴身衣物,咬住,难捱地扬着暴起青筋的脖颈,他快要窒息的眼神迷离,真想把这疯狂的一幕拍下来发给她。告诉她,我在你的冷脸下得好痛快。第四天。“她跟你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没有。”“她有亲口承认你俩的关系吗?”“没有。”“……那你现在又在给人家当免费保姆?”萧骋真是要疯了:“她家大业大的不知道请保姆吗?折腾你算怎么回事?”“你知道别人要是有你这双手恨不得供起来吗?只有你不当回事用它洗衣做饭!”“我愿意的,”齐宿转着酒杯,“我不:()妈妈死后,我被病态男妈妈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