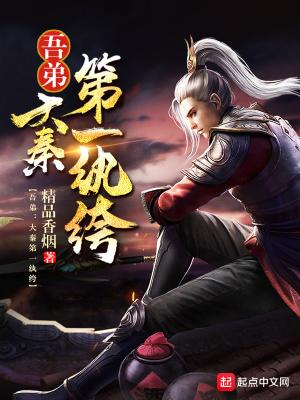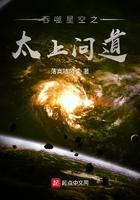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蜀汉之庄稼汉TXT全文 > 第938章 阳谋过年更新就是对大伙最好的新年贺词(第1页)
第938章 阳谋过年更新就是对大伙最好的新年贺词(第1页)
所谓唇亡齿寒,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种道理小孩子都懂,诸葛恪又怎么会不懂?吕壹连顾公都敢构陷,导致陛下有换了丞相的念头。若是此人当真是欲对太子动手,谁知道最后会不会蛊惑陛下换了太子?说句不敬的话,太子生母太过卑贱,而养母又被陛下遣回老家。谁真要敢保证说太子地位稳如泰山,那此人不是蠢到家就是别有用心。要不然殿下为何常常当众说,愿意把太子之位让给三皇子孙和?一念至此,诸葛恪便安慰孙登道:“殿下莫急,依吾看来,吕壹此举,怕不过是他个人所为,身后当是没有他人。”“为何?”“殿下想想,如今有能力威胁到殿下的太子之位者,都有何人?不过三皇子一人耳。”二皇子孙虑,前两年刚被封为镇军大将军,甚至还未封王,便已卒世。“然三皇子年不过刚逾十,又与殿下亲厚,那吕壹总不可能是为三皇子谋求太子之位吧?”“再说了,陛下又岂会废长立幼,徒乱国本?”陛下嫡妻本是谢夫人,只是谢夫人早逝,后面又娶了徐夫人为正妻。谁料到徐夫人最后却被遣回了老家。直到现在,陛下一直都未曾册立皇后。故所有皇子,从身份上来说,没有高低之分,只有长幼之序。最多不过是看谁人母亲得宠。故陛下欲行废立太子之事,则必先册封皇后。当年陛下称帝,欲立步氏为后,然群臣坚持立徐氏。皇后之事,就这么一直拖而不决。故封后之事,兹事重大,非皇家私事,就连陛下都不能一言决之。想通了这一点,诸葛恪于是对孙登说道,“臣以为,这吕壹乃是私下之事,当无他人指使。”“武昌本就是殿下当年的镇守之地,殿下屡次上书,劝谏陛下不可重用吕壹。”“而远在武昌的上大将军、潘太常亦与殿下同,在吕壹看来,乃是由殿下指使。”“故吕壹构陷殿下身边之人,原因正在于此。”孙登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即便是如此,亦不能让此等小人蒙蔽陛下,不然长久以往,只怕就要令朝中众臣离心。”诸葛恪沉吟了一会,然后摇了摇头:“殿下与上大将军数次上书,亦难改变陛下对此人的看法,可见其深得陛下信重。”“骤然之间,怕是难以动摇他在陛下心里的地位,唯有徐徐图之。”孙登闻言,不禁有些失望:“元逊也没有好办法吗?”诸葛恪淡然一笑:“吕壹小人,无根无基,能在众臣面前作威福者,不过是仗着陛下亲信罢了。”“别看现在此人气焰滔天,但若是哪一日陛下对其生疑,便是身首分离之日。”孙登叹息:“何其难也?”“不难!”诸葛恪摇头,目闪冷光,“吕壹之威福,全系于陛下,若能想办法让陛下疏远小人,则我等诛之易耳。”“如何个疏远法?”“须得先有人敢面陈陛下,当面指出吕壹所为,说动陛下,查吕壹此人所为,否则我等做再多,亦是对此人莫得奈何。”孙登越发地皱眉:“朝中论起身份贵重者,莫如上大将军与吾,我等屡次上书,皆无法说服陛下,更何论他人?”诸葛恪哈哈一笑:“殿下,正因为是朝中人,所以才说不动陛下啊。”“殿下想想,陛下令吕壹任中书典校郎,正是为监察百官。”“如今百官上书弹劾吕壹,不正是说明吕壹监察有方?”“所以上书者逾众,只怕吕壹受陛下亲信就越重啊!”孙登闻言,恍然大悟,一拍大腿:“此言甚是!吾竟是没有想到这一层!”说着他看向诸葛恪,赞叹道:“元逊,幸亏有你!”诸葛恪略有自得地一笑,他自然不会说自己也是刚想通这一层。只听得他继续说道:“殿下,所以这个面陈陛下的人,非但不能是朝中之臣,甚至连地方州郡官吏亦不可选。”中书典校郎一职,不仅仅是监察中央百官,地方州郡亦在监察之列,看似位卑,实则权大。“如此说来,这等人物,只怕是难寻啊!”即便是百官中,单独面对陛下时,亦有不少人会惶恐。更别说是直言吕壹之过,极有可能会受到吕壹的报复。所以这个人,不但要大胆,而且还必须不怕死。吕壹得陛下所重,想要说动陛下,必须得能言会道。说好听点是能言会道,说难听点,那就是巧言令色。想起巧言令色……孙登连忙甩了甩头,把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事情来。敢直面陛下,不惧生死,不怕吕壹报复,又不能是官吏,所以只能是在民间找。但民间哪里能寻得这等人物?!苍头黔首连自己的姓名都不知怎么写,更别指望他们能说出什么道理。,!甚至还是在陛下面前论说治国大道理。似乎那巧言令色之徒也是诸葛亮从民间简拔,而且未入仕便已献出定南中之策……真烦!烦死了!明明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偏偏又卡在了关键人物身上,顿时就让孙登烦躁起来:“难道吾等当真拿此等小人毫无办法耶?”“我们寻不得,他人未必就寻不得。”诸葛恪却是从容地说了一句。“谁?!”孙登连忙问道。“羊衜。”“他?”孙登面露狐疑之色,看向诸葛恪,目光闪了闪。“没错,就是他。”诸葛恪点了点头,肯定道:“羊衜有识人之明,此世人所知。若是他能发掘民间才智之士,举荐于陛下面前,陛下定不会有所疑。”说到这里,诸葛恪脸上露出冷笑,“若是此才智之士,直言吕壹之过,殿下觉得陛下会怎么想?”怎么想?毕竟这位才智之士可是从民间发掘,现在连民间都知吕壹乃是阴狠小人,陛下岂能还蒙在鼓里?“妙啊!”孙登已经把大腿拍疼了,他满面喜色,“此计大妙!”但见孙登咬了咬牙,继续说道:“元逊说得没错,羊衜确实是有识人之明,此事交给他,最是合适,若是他不答应,吾便求到他应下为止。”诸葛恪微微一笑,胸有成竹:“殿下放心,他定会答应的。”既然你敢屡次直言东宫众人之失,要做一个敢言正直之士,那这等为国分忧的事情,总不能退缩吧?要不然,岂不是成了虚伪好名之徒?解决了一件长久压在心头的大事,孙登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举起茶杯,想要喝口茶,这才发现茶已经凉了。于是他又连忙亲自给诸葛恪换了一杯热茶。诸葛恪看到孙登这般举动,心头就是一动,试探着问道:“殿下……还有他事?”孙登点了点头,却是没有方才那般阴沉之色,只是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道:“陛下封元逊为威北将军,其意不言自明。在吾看来,就算是元逊不自请过江,只怕陛下亦会派元逊过江击贼。”“这不是好事么?”“是好事。”孙登目光盯着手里的茶杯,良久才低沉地说了一句,“不过有一件事元逊你可能不知道。”“前些日子,魏国皇帝曹叡派了使臣过来,向我大吴提出,愿意以战马换取明珠、玳瑁等宝物。”诸葛恪闻言就是一笑:“常闻曹叡喜好明珠,如今倒是亲眼……”话未说完,他就猛地顿住,身子都不由自主地坐直了,向孙登看去。孙登抬起眼眸,与他对视了一眼,然后又再次垂下眼眸,继续呆呆地看着手里的茶杯。诸葛恪咽了一口口水,问道:“陛下……答应了么?”孙登点了点头,声音仍是低沉:“应下了。陛下言,明珠、玳瑁者,于吴国不过如石块瓦砾,然却可换来战马,增我大吴军中之力,何乐而不为?”诸葛恪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勉强笑道:“陛下明鉴,应当就是这样了。”孙登嘴角扯了一下,就当是笑了。当年陛下对魏国称臣,曹丕向大吴索要宝物,陛下也是这么说的。唯一的区别就在于,那个时候,曹丕是索要,而现在,曹叡是拿战马来换。毕竟……今日不同往昔啊!大吴国主,可不再是魏国所封的吴王了。而是大吴皇帝。不过孙登仍是总觉得心里膈应得慌。诸葛恪仿佛看出了孙登的心思,安慰道:“此事陛下并没有隐瞒,正说明陛下心胸坦荡,没有别的心思。”“况且蜀国与魏国之间,不也有商队往来?现天下三足鼎立,相互之间换取些东西,也是正常之事。”蜀魏之间有商队往来是没错。可是蜀国现在的物资那般抢手,也从未听说过曹叡会亲自派出使者与刘禅交换物资……只见孙登叹了一口气:“我怕的是,此恐曹叡离间吴蜀两国之计耳。”事实上,这一次曹叡很是大方。所给的战马不但数量众多,足有千匹。而且价格很公道,甚至可以说是让大吴占了大便宜。孙权屡次派人前往辽东,带了无数的奇珍异宝,给公孙渊又是封官又是晋爵。换回来的战马都没有这一次曹叡来得有诚意。但也正因为占了这么大便宜,孙登心里才隐隐觉得哪里不太对。听到孙登的担忧,诸葛恪沉默了一阵,最后也跟着叹了一口气:“即便是离间之计,我大吴亦不得不收下这些战马。”天下谁人不知大吴战马紧缺?魏贼有并幽二州,蜀国有凉州陇右。唯有吴国,屡次欲交好辽东而不可得。曹叡这一次,算是拿捏住了陛下的心思。千匹上好的战马,对于吴国来说,实在是太多了,多到吴国君臣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但吴魏两国断绝交往已有十年,现在突然有了往来,而且还是两国国主之间的往来,谁敢说蜀国不会起了疑心?就算是不起疑心,只怕蜀国君臣心里头也会不痛快。毕竟荆州之事,永远是吴蜀两国绕不过去的疤痕。更何况吴蜀可是起了祭坛,燎火告天,公开誓盟。若是吴国再在暗地里背蜀而和魏,怕是天下人都要笑吴人无丝毫信用。到时吴国君臣,如何立足于世间?“殿下既有此忧,何不告知陛下,也免得吴蜀二国之间,生了嫌隙?”“吾又何尝不想?”孙登苦恼道,“只是一来吾未知陛下心中究竟是何想法。”“这其二嘛,则是谤讪国政一案,风波未平。吾若是行错一步,被吕壹抓住机会,在陛下面前进馋言,只怕……唉!”说到这里,孙登与诸葛恪对视一眼。两人心中都有了一个决断:吕壹此人,已是朝中大患,必须及早除去才行!“殿下若是不方便,何不让上大将军进言?”诸葛恪提醒道。孙登仍是有些犹豫:“事到如今,吕壹十有八九是欲对吾不利。”“若是吕壹对陛下进言,吾居东宫,却与武昌的上大将军书信往来频繁,甚至还能指使上大将军。”“到时陛下问起,吾又如何解释?”身为太子,孙登既是君,也是臣。陛下在登上尊位后,重用吕壹的原因,孙登也是明白一二的。说白了,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百官群臣。只是这等帝王心术,可意会不可明言。上大将军镇守武昌,半个吴国皆在其掌握之下。若是自己仍在武昌还好说,与上大将军商量国事乃是正常之事。但现在自己已回建业,若是仍与上大将军有密切往来,甚至一封书信就能说动上大将军。那可就是不知进退,犯了禁忌啊!诸葛恪看到孙登为难,当下便自告奋勇地说道:“若是殿下不便直接与上大将军商量此事,那吾便写信给大人,让大人把殿下心中之忧,转告给上大将军,如何?”孙登大喜,上前握住诸葛恪的手:“如此甚好!”诸葛瑾乃是大将军,常年镇守荆州,与上大将军陆逊交情匪浅。若是由他转告,则不会有泄密之忧。建兴十二年十月,刚占了魏国一个大便宜的孙权经陆逊提醒,认识到这很可能是魏国的离间之计。当下猛然醒悟,很快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蜀国。谁知道这个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信使在过江夏,准备进入南郡地界的时候,偏偏就遇到了南下劫掠的小支魏军。这封信,最后自然是落入了魏军手里。然后被魏军以最快的速度,送至洛阳。这些年来,魏吴两国在荆州的边境,虽少有大战,但双方小股军队相互入境劫掠之事经常发生。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孙权在得知此事后,也没有太过在意。只是又重新写了一封信,准备再派人送到诸葛亮与汉家天子手里。ps:吴国荆州边境因为地形复杂,加上水网密集,所以双方常有小股军队入境骚扰。吴国不止一次被魏国截过信。就连历史上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的前一年,孙权写给诸葛亮相约一齐进攻的信,都曾被魏国截住。这就是吴国荆州没有襄阳这种险要之处来防守的无奈。:()蜀汉之庄稼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