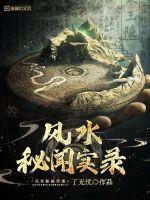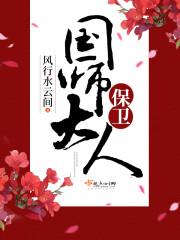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蜀汉之庄稼汉TXT全文 > 第1038章 巨变(第1页)
第1038章 巨变(第1页)
管仲之术也好,经济殖民也罢,基本上套路都差不多。前期先要投入大量成本,培养扶植代理人或者利益集团,在不知不觉中瓦解敌人内部,让敌人按自己的设计走。只待时机成熟,再进行收割。想要实施这个套路,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自身的实力一定要够强——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用直白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若是半路上搞到一半,因为自身实力的衰弱而搞不下去了,前期对他国的投入就真成了割肉喂狗。说不定最后还会被反噬。当然,若是能顺利收割敌人,收获也是巨大的。即便不能灭国,最低也能奴役他国为己所用,或者让敌国不战自乱。所幸的是,现在的大汉对于吴国来说,是强国。人口,经济,军事,无一不在吴国之上。更重要的是,在收复了关中并州河东之后,假以时日,大汉的战争潜力,迟早是三国之最。战争潜力,看的不单单是谁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还要看谁能更好地进行战争动员,谁能把国内资源更高效率地加以运用。从这一点上来说,大汉已经与吴国与魏国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至少在十年前,冯刺史就已经开始在地方尝试恢复前汉,或者说前秦的乡亭制度。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十多年不间断地在地方推广学堂,培养出了一大批基层干部。退役的军中老卒,地方学堂考不上皇家学院的学生,他们就是官府掌控地方的神经末稍。从南中到陇右,再到凉州,无一不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如果说,被世家豪右完全控制了地方的魏吴两国,就如同是身上长了恶性肿瘤的病人。那么大汉,就是一个已经成功手术,正在恢复健康的年青人。十五年前,大汉丞相为了能多筹集一些粮食,不惜在国力最孱弱的时候,征发民夫清理都江堰。甚至还专门设立了堰官,领兵丁千二百人巡护水利。这个前无古人之举,说起来也是一种无奈。毕竟当时的蜀汉经济命脉,都掌握在世家手里。没有钱粮,谈何南征北战?谁又能料到十五年后,蜀地世家看着年年增产的粮食,再看看被死死地压制着的粮价,欲哭无泪。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教,蜀中世家早已经变得帖帖服服。农桑乃国之根本,蜀地平原那么一大片的耕地,哪里要种粮食,哪里要种桑树,是早就已经规定好了的。谁敢乱种甘蔗茶树啥的,官府第二天就能找上门来。至于粮贱伤农这种事情,当然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官府对粮食有一个保底价,兴汉会甚至还能高出保底价两三文钱,甚至四五文收购。反正肯定不会让大伙亏本种地就是。你就说你卖不卖吧!“你这粮价要是合适我们肯定卖啊!”锦城外码头仓库,同时有兴汉会设在蜀地的最大据点。今天这个据点,迎来了不少客人:李家、张家、赵家、黄家……蜀地但凡排得上号的家族,都派出能拿主意的话事人。听到坐在主位上的邓良,看着下边的吵吵嚷嚷,笑得很是温恭:“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我们兴汉会做事,那都是地道得很!哪一年我们收粮的价钱,不是比别人高?”那是因为除了卖给官府,就只能卖给你们好吗?!这么些年来,官府仗着有兴汉会的草场牧场撑腰,年年都有大量的耕牛租给泥腿子。八牛犁泥腿子用不上,但曲辕犁却是最适合小户人家用。这么多年战乱下来,人口十不存一可能太过夸张,但说锐减了六七成那肯定是事实。再加上丞相一直在大力兴修水利,还有这些年来,对外作战节节胜利。让官府手里掌握了大量的荒田,能够大规模地给泥腿子分田分地,而且赋税也不高。最重要的是,只有上了户籍的人家,才能把孩子送到学堂。这可算得上是大汉天子最大的仁政——至于有没有人在暗地里咬牙切齿,谁在意啊?富裕一些的农户,现在连鸡鸭都养上了。有了那么大的盼头,谁还愿意当隐户?大户人家屯再多的粮食,又有什么意义?想起这些年不少大户人家去南乡做粮食买卖,最后却是家破人亡,不少人心里都是“呸”地一声:官商勾结,欺凌士吏,你还有脸说做事地道了?“就是因为知道兴汉会做事地道,所以我等一听到这里准备大批收粮,这不就是急忙赶过来了嘛!”有人陪笑:“不知贵会想要收多少粮食?”邓良意味深长地看了对方一眼,开口缓缓地说道:“放心,这一回会里不是去南乡挂牌,而是直接知会大伙,意思就很明白:这一回只向在场的各家收粮,不会从其他地方的粮商收粮。”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当真?”在场的大部分人听了,不禁喜形于色。也就是说,这一回,大伙不用去南乡交易所那里,和各地的粮商竞争了?接着他们就看到邓良伸出一个巴掌,继续说道:“这次买的陈粮,会里可以比南乡交易所的粮价高出三成收粮,若是愿意现在就写下契书,明年可高出五成收粮。”“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让屋内的温度都冷了几分。“当真!”这一回,不单单是几个问,而是大部分人异口同声。邓良见此,又是微微一笑,然后伸出三根手指:“三份契书,双方各留一份,官府备留一份。”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真的了?想要毁约,那就是把兴汉会和官府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名声毁于一旦。众人面面相觑,皆是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有人咽了咽口水,小心地问道:“敢问邓郎君,这个事情,冯……呃,冯会首他知道吗?”从冯鬼王出山那天算起,不知有多少人在小本本记下了此人的黑帐。然而这么多年来,大伙的心气却是越来越短,有不少人甚至还患上了“鬼王恐惧症”。吃亏这么多年,突然得了这么大的好处,反而让人在第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当然,也有人心里别有他想:冯鬼王今年大半年都是隔绝消息,就算现在有可能进入长安,但按关中与锦城的距离算,两地互通消息没可能会传得这么快。既然如此,那此事除非是提前商量,否则就是有人在冯鬼王不知情的情况下,独自作出决定。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兴汉会出现了第二个龙头?但见邓良悠然道:“大伙且放心就是,这么大的事情,兄长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噫,我倒希望他不知道。咦?不对。如果这个事情当真是冯鬼王提前作出的决定。那岂不是说,冯鬼王至少在一年前,也就是出征前,就已经定下了这个事?想起某人的深谋远虑,更多的人越发犹豫起来:大伙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攒了一点钱,不会又被人看上了吧?看到众人突然间没了话语,邓良大是意外:这等好事,你们为何反倒是这等表现?“邓郎君,这些年来,我们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在座的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算是有些交情。”“你能不能大伙透个底,这笔买卖,究竟是个怎么回事?”可不是嘛,这些年来,大伙每年屯下的粮食,大部分都是卖给兴汉会了。老相识了!听到这个话,邓良终于隐约猜到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但见他不由地一笑,坦然道:“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不好说的。说白了,就是吴国荆州那边,粮食有些短缺,曾多次派人求助于朝廷。”“后来的事情,大伙也应该知道,因为要准备关中一战,所以这个事就推迟了。”“不过准备工作,却是没有落下,比如说在永安设置的易市,就是为了更方便与吴国交易。”说到这里,邓良举杯轻啜了一口茶,这才继续说道:“现在主管永安易市的,正是费公举(费诗),此人本就是蜀地人士,为人耿直敢言,大伙若是心有疑虑,不妨前去询问一番。”费公举?唔唔,这个嘛……先是上书反对刘备过早称帝,后又当面反对诸葛亮接受孟达的投降,费公举的人品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至少比某冯姓的家伙强多了。荆州粮价高——整个吴国的粮价都要比蜀地高上许多——这个事情,大伙早就有所耳闻。但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运粮出境,卖给他国,那可是杀头的买卖。特别是以蜀地的地形,就算是有胆子豁出去,那也没有办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把大批粮食运到荆州。在苦寻多年无路的情况下,现在终于放开了一个口子,要说不心动,那肯定就是假的。“邓郎君,敢问这一次,要收多少粮食?”在场的没人是傻子,以邓良眼下的言辞看来,这个事情,至少已经有七八成是真的了。于是气氛立刻就稍稍有些热烈起来:“是啊邓郎君,这一次卖多少粮食给东边?”“自然是多多益善,毕竟兴汉会每年都会在蜀地收粮。”“当然,高价粮只会卖往荆州,所以肯定是有配额的,这个要看荆州那边的缺粮情况而定。”原本得知可以卖粮给荆州后,别有心思的人,听到配额二字,心头顿时就是一凉。那岂不是说,给荆州卖粮仍是要受到管控?那岂不是说,只能卖一部分高价粮?那岂不是说,我们不能自己运粮去荆州?入他阿母的!不要脸的东西!一天到晚尽是官商勾结!“邓郎君,你是知道的,大伙手里的粮食,从来是不会缺的。所以这高价粮的配额,究竟是个什么章程,能否详细说说?”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兴汉会锦城堂口邓堂主闻言,微微一笑:“这个嘛,章程自然是有的。不瞒大伙,我得到消息,朝廷可能会在蜀地各郡开办学堂。”“只是大伙也知道,关中一战未定,朝廷的府库恐怕不太宽裕……”话未说尽,眼神提示:你们懂得!谁不知道,兴汉会其实就是天下最大的白手套?邓堂主能提前知道一些内幕消息,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只是府库不太宽裕是个什么意思?你家阿翁过来是想赚钱的,你居然想让我掏钱?不过学堂……学堂?!“邓郎君,你的意思是说,朝廷终于打算在锦城开学堂了?”几年前凉州第一次考课结束,就已经有人在鼓吹,想要在蜀郡建立学堂。这个提议送到汉中后,又被大汉丞相转给了冯鬼王,询问他的意见。而冯鬼王给出的最终答复是:南乡师资和教材太过紧张,暂时无力支援蜀郡的学堂建设。“不仅仅是锦城,还有蜀郡周围的数郡,都会建立学堂,所需的钱粮,肯定是少不了的。”“这学堂之事嘛,兴汉会自然也是掺与其中的,所以这收粮一事的章程,还是要落在学堂上。”“这可是大善事啊,可是少有的仁政啊!”有人顿时就激动起来。那可不?好人要有好报嘛,学堂一事,谁出的钱粮多,高价粮的配额自然就会多一些。不过这对于蜀地世家来说,也算是久盼之事。因为只有开了学堂,才算是真正有了进入皇家学院的渠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还得七拐八弯寻找门路。甚至有很多时候,连门路都找不着。有人已经忍不住地大声道:“学堂的钱粮之事,邓郎君不必担心,吾等身为蜀在人士,若是坐视不理,那可是要被乡亲们戳脊梁骨的!”不少人算是看出来了,这所谓的高价粮根本就是一个借口。其实就是有人想要借邓良之口,试探大伙对学堂的看法——当然,高价粮还是要卖的,能赚一点是一点。只是,为什么诸葛村夫和冯鬼王会突发善心?给大伙又是送钱,又是疏通蜀中子弟的仕途?怀着这个问题,谯周悄悄地前去拜访蜀郡着名学者杜琼。此时秦宓已经去世,左中郎将杜琼成为蜀地本土官吏最德高望重的人之一。杜琼平日里沉默寡言,少见外人,这一次却是难得地接见了谯周。“关中一战,非但是天下之巨变,同时也会是大汉的巨变。”他看向外头的桃林,此时已是桃叶尽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现在的大汉,可不是十多年前,只靠蜀地苦苦支撑的模样。而是已经坐拥天下形胜之地,隐有兴复之势。这十余年来的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天子乃明君,丞相乃明相,朝中有识之士颇众,又岂会看不出大汉局势之变?知其变而适其变,可谓俊杰之士乎?”谯周听不懂,只好虚心地问道:“请先生详解之。”杜琼问道:“当年蜀中世家被丞相与冯君侯所恶,你可知为何?”谯周张了张嘴,却不敢多言。杜琼似乎早就料到了谯周的态度,自顾自地说下去:“蜀中豪右之所为,多是阻碍大汉还于旧都之举,今日境地,可谓自取,但凉州豪强难道就都是清白的吗?”“关中一战,大汉不但尽复关中,而且还掌握了并州河东等地,北方的世家,难道就全是希望大汉兴复的?”伪魏篡汉,要说没有北方的世家支持,谁信?谯周似乎抓到了什么,他瞪大了眼,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先生的意思是说,朝廷欲行平衡之术?”杜琼的目光再次看向桃林,缓缓地说道:“当年朝廷借凉州豪族之手,打压蜀中世家,现在就算是换了一个打压对象,也不过是故计重施,有何奇怪?”河东是世家林立之地,谯周自然是明白的。只是朝廷向来重凉州而轻蜀中,就算是要打压中原世家,为何不直接继续借重凉州豪族之手?谯周想到这里,心头不禁就是颤了一颤,他压低了声音,悄悄地问道:“先生,如果当真是朝廷的平衡之术,那岂不是说,凉州也有可能……”“那不是你我所要操心的事。”杜琼的目光淡淡地扫了一眼谯周,“你看,此时正徝寒冬,那桃树有如枯死。”“而一月之后,它却将会长出花骨,绽放芳华,美不胜收。”杜琼语气幽深地说道:“蜀中子弟已经失去了一次最好的机会,这些年来,就如窗外的桃树,受尽寒风。”“这一次,可谓是历尽寒冬,迎来暖春,若是再不长芽开花,那可就是真要被人当成枯枝砍下当柴火了。”:()蜀汉之庄稼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