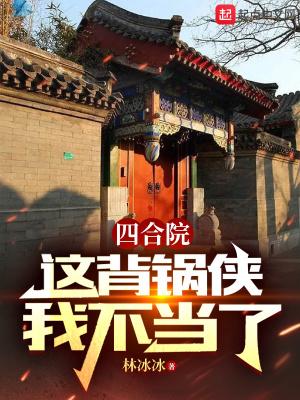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被休但成为女帝免费阅读 > 第214章(第1页)
第214章(第1页)
“你笑?什么?”司马恒不快地说道。
“我在为公主?高?兴。”郗归看着司马恒,内心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愉悦。
人生在世,无能为力?之事?实在太多。
譬如她明?明?已经辛苦筹谋,可吴兴却依旧发生了伤亡惨重的意外。
可尽管如此,她还是依旧相信,只要坚定?地去做,那?么结果哪怕没有那?么好,也会远胜从前。
凡所?做过的事?,全都不会了无痕迹。
其痕迹或是在世上,或是存留在,某个人的心上。
郗归清楚地察觉了司马恒的变化?,就?像她在一封封来自吴地的条陈中,敏锐地察觉了郗途的变化?一般。
他们原本都是这个旧时代坚定?的拥趸,为了自身利益而天然?地维护那?个业已衰落的王朝,从未对此产生过任何怀疑。
可郗归改变了他们。
吴地的所?见所?闻让郗途越来越相信郗归所?说的一切,他渐渐地由单纯地为家族而战,向着为苍生百姓而战的宏远目标靠拢。
而司马恒,这个锦衣玉食的公主?,这个曾不止一次地以婚事?为手段谋取未来的女人,终于下定?决心,想要开启另外一种生活。
郗归正式向司马恒发出了邀约:“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教授女军或是蒙学里的孩子们,可以一步步地学着处理一村一县乃至一郡的政务,可以帮北府军管理名下商铺,也可以像兰台令史一般校勘图书、整理经籍……”
司马恒一桩桩地听下去,觉得每件事?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我不爱与小孩打交道,尤其是那?些冒冒失失的愚笨小孩。”
司马恒已经生育过三个孩子,可却从来不觉得小孩可爱,也不认为自己应当被?母职捆束。
孩子的哭闹总是让她心烦,她讨厌这种不能够理性沟通的无知生物。
“至于政务,你定?然?不愿意让我从大官做起,可我堂堂公主?,又怎能去村县理事??”
在司马恒的眼中,下民们大多肮脏愚蠢、粗鄙不堪,她自小生活在宫闱之中,难以想象自己放低身段去与那?些小民接触的情景。
“至于商铺,那?就?更加不可能了。士农工商,商乃最末流者。我身为公主?,怎可自轻自贱,去行那?商贾之事??”
司马恒想到平日所?见商铺主?事?谄媚的模样,觉得自己若要那?般奉承别人,倒还不如直接去死。
“校书也没什么意思,似那?般成日坐在竹简堆里,闻着旧书古籍的霉味,日复一日地守着书卷,一年年地把眼睛看瞎,哪里是人该过的日子?”
郗归别有深意地看了司马恒一眼,竟看得她心里有些发怵:“我真不是故意挑刺,实在是你说的这些事?,我全部都做不来啊!”
郗归无奈地笑?了:“公主?,我以为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你说要靠自己的努力?掌握权力?,那?就?势必要走?出原本的舒适圈,去尝试一些从前不曾做过的事?情。否则的话,又何谈改变呢?”
“徐州并不是一个很小的地域,其中有无数个可以让人从中获得进步与成长的位置,你可以与我一道回?去,仔细看看,然?后再好好地思考一番,看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坦白?讲,对于司马恒的反复与犹豫,郗归难免有些怒其不争,可当她想起自己曾在江左蹉跎的二十余年后,又觉得不该责怪司马恒——作为一个拥有现代灵魂的后世之人,她也是在至亲死亡的悲恸之下,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应该与这种看似美好的牢笼生活决裂,真正为自己而活。
既然?如此,司马恒作为一个古人,其犹豫又有何奇怪呢?
郗归心念转了几分,最终只是平静地说道:“公主?,通往权力?的道路是如此地漫长,我们也许会遇到无数的敌人,可真正能够在这条路上拦下我们的,永远只有我们自己。”
“去京口看看吧,你还年轻,完全可以尝试不同的生活。如果最终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你。”一道惊雷炸响,大雨更为猛烈地砸了下来,郗归脑中有些恍惚,放任自己打了个呵欠,“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外面雨大,请公主?暂且在营地里避避雨吧。”
司马恒还要再说,郗归却轻轻摇了摇头:“没关?系的,公主?,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都只需要对自己负责,我不强求什么。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朱、张二氏不会再有反抗的余地,三吴之事?将再无悬念。你若公开支持我们,自然?是一桩锦上添花的好事?;可若不表态,我们也不会有何损失。你回?去好生想想吧。”
这场司马恒强求得来的对话,就?这样终止在了她自己的抗拒之中。
司马恒并不愿意就?此离开,可南烛已躬身候在一旁,司马恒的骄傲不允许她死皮赖脸地强留。
大颗的雨珠砸在地上,溅起一个又一个泥点,落在司马恒华贵的裙摆上。
她坐在一座空闲的营帐之中,不快地看着护卫跪在一旁,帮她拧干裙摆上的雨水,擦拭其上的脏污。
可丝缎娇贵,很快便成了皱巴巴的一团,宛如一朵开败的花、一池秋日的荷,干枯丑陋,了无生意。
司马恒蹙眉挥了挥手,示意护卫出去等候,不要再在眼前碍眼。
她一遍又一遍地想着郗归方才?所?说的话,不得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可又实在无法说服自己去从事?那?些事?务。
直到护卫重新出现在门口,她才?从纠结中清醒过来,意识到天边已然?露出了微白?地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