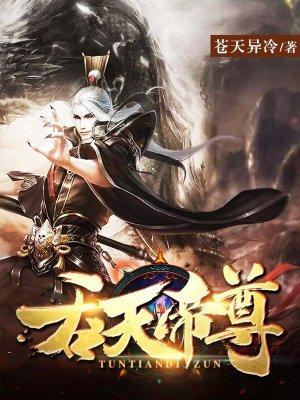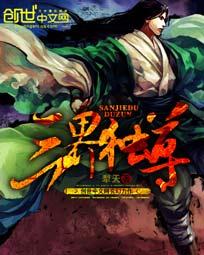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心中下了一场雪 > 第221章(第1页)
第221章(第1页)
年轻的医生站在他们的旁边,面容英俊,气质干净秀气,随着他们走近的脚步,也抬头望了过来跟闫怀峥对视着。
陈院的声音温和。
“来,怀峥,这就是小江,江述宁,你们之前在藏区应该见过面,以后在新院区算是你的副手了。”
————————————————————
缝线剪断。
头灯的光束将眼前小小的胸腔里所有大血管通路全部照亮。
林远琛检查过心肺间所有的操作,补片与缝合口的位置和做法,刚才陆洋做的部分用的方式比之前两次要更加精简,加大的流出道和肺血管的吻合通路每一处看着都没有差错。
接过了器械护士递过来装在注射器里的生理盐水,注水测试模拟着血流动力,检查着瓣膜间是否会存在反流的情况。
陆洋在一旁同样专注地看着,这个孩子的虽然症状不重,但是对于肺血管连接的重建和改道,效果能不能一样幸运,结果令他紧张。
“还行,微轻度返流,”林远琛看了陆洋一眼,“手术前第二例的小女孩已经成功关胸,这次又做了改良,你可以开始准备总结和归纳了,理论加上实践经验,慢慢起初稿吧。”
一边说着一边也再做了一些修补,然后告知其它的手术医生,开始准备撤体外循环,复温复跳。陆洋点了点头,手上也辅助着他的动作,孩子的情况很好,一切都很顺利,如果后期恢复得好,按照预计也不会出现梗阻,关胸缝合,即便是陆洋处理着善后的工作,林远琛也没有出去,一直看着他把所有的事情做完。
家属乌泱泱快十个人全都守候在手术室的楼层的走廊上,林远琛没有让陆洋跟去,陆洋便同住院医生一起护送着孩子被推进了儿童监护室。
依然是按照惯例的跟监护室管床的住院医和负责护士交接了一些注意事项,陆洋回到值班室里坐下喝上一口冰可乐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算是活过来了。
刚刚在手术室的生活区洗过澡,身上还带着一点潮气,头发也没吹得全干,今晚还有一些工作要做,等会他还想去护士站和病房看看,所以不急着休息。
打开了电脑里当时记录的楷楷每天体征的数据,还有一系列病程病历,所有小结和记录,陆洋扫过日期,才恍然反应过来,自己做这个住院总,原来已经还是三个月左右就满一年了。
时间的确是在忙忙碌碌中过得最快,自己也难免感慨。
母亲发来了微信,说着检查已经做完了,五到七个工作日内会通知去拿报告。在一件件积压于胸口的事情中,静下心来整理数据都算是一种休息和暂时的躲避。
空调的温度不低,但也许是深夜,所以渐渐会下意识地觉得有些凉意,陆洋拿过一旁的薄外套披在了身上,几分困倦在这时候也缓慢地席卷着高速运转的大脑。
他在夜里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阵。
走廊苍白的灯管有的时候就像是医院里人为造出的月亮。
急匆匆地奔走过走廊,灯光又会在某个刹那如同日光一样强烈到晃眼,衣角被带起的风扬起,无论寒暑,每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行走,四肢到身躯,每一寸血液,每一分心跳都好像是凉的,总是一阵接着一阵地发冷。
多巴胺、肾上腺素、米力农口头医嘱一道接着一道地下,配比,推注,泵入,护士的操作迅速,人影不断地在视线里穿梭摇晃,一阵阵地遮蔽过灯光。
情况的转变往往都是来得突然,速度和程度都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所拿捏,所有的挣扎与拼命都像是一场在短暂时间里的漫长拉锯,一分一秒都要争抢,汗水已经浸润透了衣物。
焦灼。
意识在极度清醒与时不时袭来又迅速消散的轻微的昏沉之间来回交替。
望望的情况在eo撤除不到二十四小时后,出现了恶化。
看着仪器,药物,尽力地拉扯起血压,耳鬓的汗水都像是冷的一样,陆洋甚至都能清晰地感知到从脸庞滑落下来的轨迹。
“很艰难。”
新生儿科的主任也忍不住擦了擦额头,林远琛大概还有五分钟到医院,连墙上的时钟都感觉走得异常缓慢。
一次次请会诊的通知,一声声仪器运转的动静,即便是在夏日也一如寒夜,所有的数值都是勉强的状态,这已经是站在拔河的中线尽全力拉回的结果,摇摇欲坠,一旦崩溃连绳端末尾都抓不住。
“用的抗生素也都是根据痰培养的结果开的,本来是明显有控制住的。”
“不应该的啊,真的不应该的,本来一切指标都是在好转的呀。血流动力也稳定,呼吸血氧都在慢慢好起来。”
但是现在站在临界的情况让所有人都有些措手不及,几位年长的医生一样是一身无菌衣,站在监护室内围守在患儿边上,热得流汗但是手掌都带着微凉的温度,困惑与疑问也一样围绕在眼前。
在病痛真实的难题面前,有时多年的临床经验,丰富的理论知识也会显得渺小。
林远琛在刚回到家两个小时不到,又披星戴月来到医院,再次出现在了外科住院大楼,消毒过后,进入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救命的机器并非万能,甚至在脱离之后有时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所有的手段都并不是绝对的。
“情况其实算是暂时稳定下来。”
但是再崩溃衰竭一次,便回天乏术了。
作为父母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告病危通知书了,坐在对面的医生讲了许多的情况说明,而孩子的母亲就像是已经流干了眼泪,憔悴的面容上没有泪水,红肿的眼睛里干涸寂静,整个人都如同脱水了一样,光明和色彩都仿佛已经褪去,身边的丈夫搂着她的肩膀,但是对于这样的肢体安慰,她好像全然没有知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