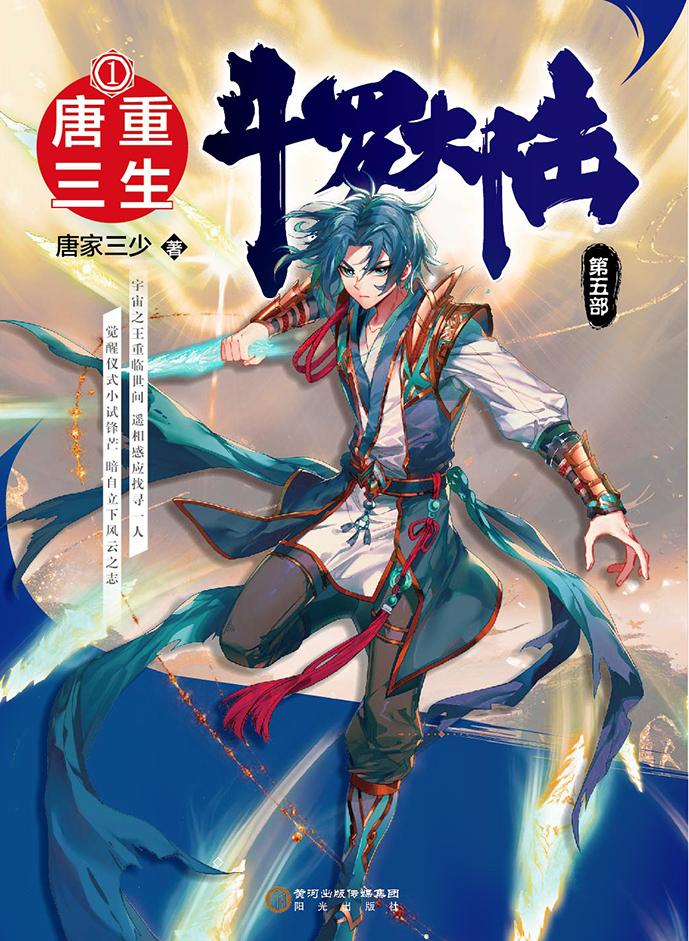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凤尘泪 > 第126章(第3页)
第126章(第3页)
沈素节说:“人不少,为首的就是那位章谊章相公,和他的儿子一起,掉了几天‘忠旧君爱故国’的鳄鱼泪,现在攀上了帝师刘令植,拍卵捧腚的丑模样你是没见到!见者欲呕!”
高云桐冷笑道:“不然我当年为何以太学生的身份以卵击石来弹劾他!他在汴京时,无非就是仗着会写青词,博得了官家的青睐。有一回为了凑趣,堂堂宰相亲自脱靴上树给官家捉猫,官家都看不下去了,喝令他有点大臣的体统,赶紧下来。他笑眯眯道:‘官家的猫下来,臣才下来。’用的是勾栏里花旦的戏腔。皇帝前乖顺,人后却无比狠毒,挤掉了朝中、地方好几位正直的臣子,只为任用自己的私人。”
沈素节说:“现在也差不多。见了刘令植叫‘相公’,见到故主,呵呵,已经皮笑肉不笑地叫‘昏德侯’了。”
“官家有自由身?”
“哪能呢!”
“那章谊居然能见到官家了?”
沈素节说:“所以是彻头彻尾降了嘛,我这种,靺鞨还防着呢。”
两人摇摇小酒坛,坛子已经空了。
牢骚虽多,发也发不完,最后还是要互相说声“保重”。
亦怕一起出去招眼,沈素节先行离开,接着才是高云桐。
高云桐不知道何娉娉遭遇了什么事,到楼下广厅里,打算与那日日在此唱曲儿的歌伎问上几句。
不料却大意了,他刚喊了一声“小红小姐”,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哦哟哟,原来叫小红,还只有你相好的知道你的名字么?”
那人边说边回头,笑容亦是瞬间凝结在嘴角。
高云桐惊了一瞬,然后笑着拱拱手:“好久不见了,该小弟请您两杯酒。”
那人冷笑道:“不敢不敢,翻覆小人莫过于君。我可不敢领教。”
高云桐笑道:“若论翻覆,无非也是学来的,天下无人出节度使之右!”
那人色变,冷笑一声:“耍嘴皮子我是耍不过你,不过……”斜眸四下环顾,想必还有不少他的人就在附近。
高云桐笑道:“乔都管,我没有带人来,不过我也不怕。”
挑挑眉毛,毫不在意的样子,瞥着上首那歌伎道:“小红,近几日有没有新曲儿?”
小红是私倡,平日靠客人打赏过活,眼力见儿极好,顿时笑道:“哎呀,高都管没有新曲儿,奴奴哪里有新曲儿?是不是高都管要打赏奴奴一阕新词了?”
高云桐看看乔都管:“没事,我跑不了,也不用跑这是靺鞨的地界。倒是久别重逢,他乡故知,难道见面就剑拔弩张的?我新作了一阕《千秋节》,是小红最擅长的调子,你不来听一听?”
小红立时对乔都管说:“官人这可一定要听一听。”眼风一斜,顿生妩媚。
乔都管这个人什么都好,唯有“色”字一关过不去。
再想想高云桐逃也逃不掉,也不像想逃的样子,说不定他另有攀援,所以不必畏惧;而自己恰恰是人生地不熟的,来析津府的目的是为义父进一步阿附上新太子幹不思,若冒失于不该自己多管的闲事,反而给义父帮了倒忙。
于是决定还是后发制人,先探探高云桐的口风再说。
于是,乔都管笑眯眯看着媚嗒嗒的小红:“难得见红颜一笑,意醉心迷,正是古人说的‘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我洗耳恭听呢。”也颇好转文。
小红对高云桐努努嘴:“喏,高都管,就等你了。”
高云桐也不言声,要了纸笔,写了一曲《千秋节》,小红看了一遍,击节道:“真是词曲缱绻,我试试。”
调好柳琴琴弦,舒开喉咙唱起来。
曲子配着词,果然曼妙非常。
高云桐笑道:“此曲当配荼蘼香酿。”看着乔都管再次问:“不与我一起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