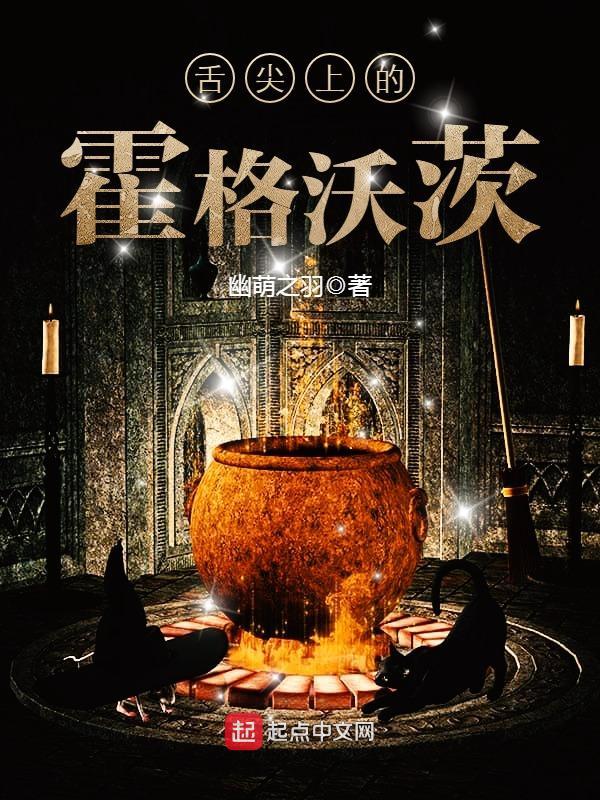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汴京酥礼 > 第115章(第1页)
第115章(第1页)
一千五百贯,也有些贵。刘家放弃了,宁愿去外城开铺子,远一些,但盘一间铺子价钱低了一大半。沈渺么,其实也有些意动,她也盘算了一下自己的身家,犹豫过后还是没出手。
她其实早有扩店的念头了,如今沈家铺子里最多能摆五六张桌子,即便门口再摆三桌,也还是太少了实在坐不下,前几日她在后宅院子里与门口巷道里也摆了几桌,那更是无奈之举了。
若是她常年这般侵占巷子,邻人如今不说,但迟早会不快。与其惹出事端,不如多盘一家店,这样两家打通合并,铺子里宽敞了,能坐下的人也多了,既不用占据“公共通道”,也能显得干净整洁一些。
除了这条路,沈渺也想过要不要去别处租赁一家更大的铺面,但她刚在杨柳东巷打响名气,若是能继续呆在这里,还是不要腾挪到别处换个大铺子的好。而且自家的铺子不用租金,成本大大降低。
但想盘隔壁的铺子,她又拿不出这许多钱,所以便是两难了:要么咬牙借房贷当古代房奴把铺子盘下来,要么就换个地头,把自己的铺子租给别人,再去租别人家的大铺子重新开始。
不过不管是要扩店还是干脆租一间大铺子,除了银钱的问题,还有人员的问题。如今铺子小,她当主厨,有余当杂工,顾婶娘当跑堂,差不多能顾得过来。但铺子大了,翻桌率上去了,所需要的人也就多了。那样的话,以沈渺以前开一个中等饭馆的经验,起码要一个主厨,一个帮厨,两个杂工,两个跑堂。
那就得多雇三个人,这又是一笔成本。
所以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把握机遇迈开步子大步向前,还是谨慎一些,先维持原样呢?
沈渺琢磨着回了灶房继续忙,来了这里,头一回生出些烦恼。
就在她为贷款扩店还是换新铺子纠结不已时,已在书院里读了好几日书的沈济,瞪着面前灰朴朴夹着稻壳的粥,也是迟迟下不去筷子。
辟雍书院里每一顿膳食都好似周掌柜做出来的泔水粥饭,让他也生出了好些烦恼。
他记得阿姊明明给他带的是细面和脱了壳的稻米,怎会煮出来是这个模样?沈济简直想冲进后厨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成了,我要饿死了,”海哥儿忽然端着盘子坐到他身边,也唉声叹气:“这啄饮堂庖厨做饭的手艺怎会比我阿娘做得还差?简直难以下咽!怨不得每日来这啄饮堂里用膳食之人都哀声怨道。”
沈济还记得之前的事,原本不想搭理海哥儿的,但两人头一天进来交米粮时便遇上了,后来每回吃饭也都能遇上,真是奇了怪了。
不过好歹是堂兄弟,又同在一处书院读书,怎么也不好视而不见。
沈济同学舍的学子性子都还不错,没有那等掐尖要强的,也没有那等斤斤计较的,脾气都差不多。沈济和他们相处得还不错。
海哥儿在丁字号学舍,里头的学子不巧都是头悬梁锥刺股,学得废寝忘食的,睁眼闭眼上茅房都在读书,非常勤勉。这就算了,竟还有个杜甫诗狂人,每日要抄写一篇杜甫的诗句,然后再把纸吃到肚子里去,妄想自己沾了诗圣的灵气,日后也能写出诗圣一般的诗句。
海哥儿不爱用功背书,成天只惦记着吃食,但如今不同的是,他的家世在书院里只算平平,人家不稀得巴结他,又看不惯他对学业懒惰,弄得海哥儿与他们几个竟都合不大来。
因此他遇到沈济都觉得亲切了,回回都厚着脸皮凑上来,很是讨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沈济如今有了阿姊这个依靠,心境大有不同了,对海哥儿竟都生出了一丝宽容,便也懒得赶他,慢慢的,两人关系倒比曾经好了些。
如今,海哥儿便无力地趴在桌上,他这肚子空空,五脏庙全起义了,实在受不了了,便小声向沈济建言:“我们要不也学那些监生……花银钱顾两个闲汉跑腿,替我们去外头买些吃的回来?”
沈济掀了掀眼皮:“支使他们跑一回少说也得二十文,贵得很。”虽然阿姊给了他不少钱,但他在书院里一直省着用钱,钱都是阿姊辛辛苦苦挣来的,他哪里敢如此挥霍?
也不知阿姊与湘姐儿近来可好,铺子里生意如何,会不会劳累?
“我请客啊。”海哥儿跃跃欲试,“你有没有看甲舍的监生,那个宁学子写的文章?书院里到处传看抄录呢!他写自己如何吃了烤鱼,如何美味,还配有绘图,实在太诱人了!我只不过读了一遍,口水都擦湿两条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