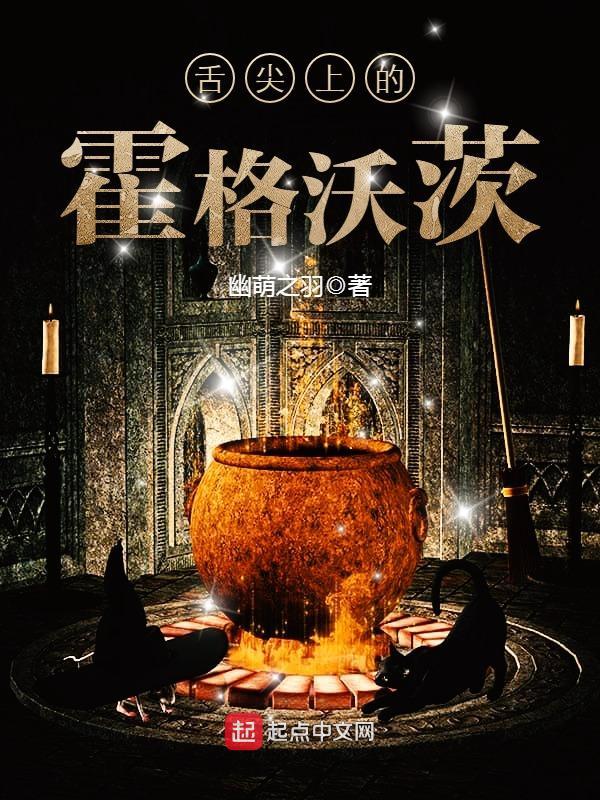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汴京酥礼 > 第135章(第1页)
第135章(第1页)
紧接着便是雨点儿般密集的拳脚,打得他头昏脑涨,鼻血流了满脸,两颗牙都叫打掉了。之后,他只能蜷在地上打滚,一面呻吟着,一面爷爷哥哥爹爹您行行好地求饶着,回应他的却只有那人更重更硬的拳头,他被打得眼冒金星,仰面倒地,罩着他的麻袋有几个窟窿眼,他隐约还看到一簇簇不断飞到夜空中,绽若繁花、灿如流火的烟火。
四处都是人,却无人察觉篙草中的动静,人人仰首望天,惊叹声声,也无人能听见他的惨呼。
瓦子里乐声高扬,真好个喜乐满人间。
顾屠苏最后一脚,狠狠往他第三条腿里踩去,踩了两脚生怕踩不碎,还用脚尖左右碾了碾,直到那两个囊袋如碎裂的鸡蛋,在他脚下彻底变得扁平了。
他这才慢慢地掀起眼看去,方才还在打滚求饶的人,此时已疼死过去,不动弹了。
踢了两脚,确信不是耍诈,他这才将麻袋扯出来。
荣大郎满脸青肿血污好似烂猪头一般,软绵绵躺在那儿,裤子中间似乎被碎掉的蛋液染深了一块儿。
顾屠苏把他衣裳脱了,随手折了几根草搓成绳,拴在他身上,略微等了等,瞅准远处来了艘货船的机会,便将他一同拉入水中,悄无声息地潜到了船尾,将光溜溜的他两只胳膊栓在那船尾端的挂网上。
这样他身子倾斜,若非遇到大浪,口鼻大多时候都在水面上,死不了。
很快,他便被那平底货船随波带走,沉沉浮浮的,一眨眼便出了汴京外城的水道闸门,只怕天一亮叫人发觉,那船都不知到哪个州府的码头了。
顾屠苏知晓他此时只是疼昏了,还有的是气儿呢,且看老天愿不愿意让这恶人得救吧。
他几乎整个身子都沉在黑乎乎的夜河里,只露出了眼鼻,就这般冷冷望着那船劈开水波远去。
顾屠苏套他麻袋时,本想着为大姐儿多打几拳出出气便算了,如今大姐儿过得挺好,也算给她积积福。可不知为何,当他的拳头狠狠打在荣大郎身上时,心口却猛然涌起一阵几乎要将他击垮的痛楚。
像有一把刀子捅进他心里,将他血淋淋刺了个对穿。
他仿佛又看见了大姐儿出嫁时那双盈盈的眼眸,她弯弯地望着他,温柔与他道别。她曾那样喜悦地期盼着,她将自己的余生都托付给了这个泼才杂碎,可是……却没落得一点儿好。
他甚至疼得还出现了破碎的幻觉:他似乎瞧见大姐儿背着比她人还高的脏衣背篓,步履蹒跚,寒冬腊月在河边搓洗衣裳,手冻得流脓;他瞧见她半夜被婆母叫起来为她倒恭桶,还指着鼻子骂她懒,扯起她的头发往墙上撞;他还看见她已瘦成薄薄一张纸,蜷在柴房的地上,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深陷空洞的眼,望向北面……
她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顾屠苏心口如锤击,双眼赤红,下手再不收着劲了。
等货船再也瞧不见了,顾屠苏上了岸。他把荣大郎的衣裳和掉落的牙齿包了石块扔进河里,又将自己那湿哒哒的褂子和裤子脱下来拧干,重新穿在身上。夏日他只穿苎麻的薄褂子和短裤,脚上也是草鞋,叫风一吹很快便干了。
他站在风口吹了会儿,因生得太黑,他几乎在夜里隐了形,哪怕有人在桥上往下望,也只能瞧见青纱帐般的篙草投下的层层叠叠的阴影,烟火一停,下头黑得更是只能看见河面微弱的波纹。
顾屠苏悄无声息地爬上河堤,重新推起那藏在桥墩阴影中的土车子,混入人流中。
回了家,家里人早都睡了,只给他留了一盏油灯。他便也随意汲水冲了个凉,还将草鞋上的泥、车轮上的泥仔细冲干净,便躺在了床榻上。
他枕着双臂,空落落地望着,他也不知自己在看什么,梁木上有只就着月光结网的蜘蛛,一圈一圈,不知疲倦地吐着丝。
他本以为自己会今夜无眠,没想到很快便睡着了。
梦里连阳光都是朦朦胧胧的,蝉声鼓噪,巷子口的大柳树丝丝缕缕垂下细辫子一般的绿枝条。好似他又回到了小时候,大姐儿的糖被巷子里其他混小子抢了,他拔腿便冲上去了,打了一架回来,鞋都掉了一只,他一跳一跳,蹦跶到脸上还挂着泪珠的大姐儿面前,伸出手,咧嘴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