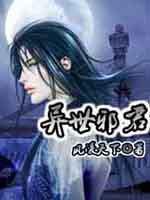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汴京酥礼 > 第140章(第2页)
第140章(第2页)
他这才能日日往沈家跑。
谢家家田多,但佃农与田奴也多,远房族人亲戚也多,自然轮不着谢祁下地。反倒金秋送爽,庄子上红枫极美,湖上残荷也别有一番意境,郗氏已带着十一娘、太夫人去城郊小住了。
唯独谢祁义正言辞借口要教沈济习武,人不能无信,所以不去。
郗氏幼时孩子管得严,得儿女大了些便懒得事事过问,一味拘着这不许那不行的有何意思?人都大了,长了腿,难道不许便不会翻墙了?
看看三哥儿以前翻墙多利索,翻得脚下功夫都练出来了,一蹦三尺高,寻常墙头都困不住他。
因此,她也随九哥儿,并不管他是去沈记当账房也好,伙计也罢。
总归是他愿意的。
说起三哥儿,郗氏又想起了谢祒从秦州送来的家信,心底又喜悦又好笑。
这家信一展开,开头,这不着调的便写道:“阿娘亲启:久未通书,至以为念,叩请福安。儿这一路,说来阿娘一定不信,九哥儿不在身边,儿竟乘船顺风顺水,乘车路途平坦,这一路几百里,连一个蟊贼都未曾遇着,如今已平安到了秦州,真是奇也幸也……”
好事成双,谢祒平安到了秦州,幽州的汤饼作坊也传了信来,说是作坊已落成,郗家的制饼匠人已照着沈娘子的方子做出了第一批汤饼,先已送往居庸关长城上日夜戍守的边军将士手中。
郗氏看完信,侧头望着窗外,笑叹了一声:“也算赶上了。”
汴京城中黄栌与银杏才开始飘叶,居庸关却已下了今年头一场雪了。边关苦寒,不知今年秋冬,他们据守边关,是否也能因此过得好一些?
第63章汤饼作坊
关山连绵,千山一白。
十月本应是秋意尚浓之际,但居庸关因地势高拔,竟早早迎来了今岁第一场雪。风裹挟着雪霰,簌簌扑进了丁号烽火台中,风声从砖石缝隙间挤过,挤得变了调子,呜呜咽咽个不停。
居庸关上这烽火台,扼守要冲,戍卒一共有八人,领头的是校尉陈忠,他是郗老将军手底下的小兵,前几年辽人饿疯了来掠边,他胆大冲锋,立下“陷阵”之功,瘸了腿,但也被郗氏的长兄小郗将军提拔为校尉。
之后便被遣派到了居庸关,日日守着这段烽火台。
天色已昏暗得瞧不出时辰,他领着手下戍卒刚结束了一趟城下巡防,人人冻得死狗一般,身上早已被雪水浸透,哆哆嗦嗦地回来后,赶忙将身上的沉重的甲胄换了,穿上补丁叠补丁的旧棉衣,升起火盆来。
戍卒们瑟缩着围坐一团,此刻歇了下来,才发觉手脚都冻得发麻。吴大紧了紧身上破得露了棉絮的衣裳,一边求身边针线好些的袍泽帮他缝补缝补,一边抱怨道:“今年这鬼天气,才秋末便能冷成这般模样,前俩月还热得狗伸舌头,如今说下雪便下雪了,我这浑身骨头都快被冻散架了。”
另一个叫李十的回来还没缓回来,身子不住哆嗦呢,接话道:“今年冷得太早了,咱们大营里发棉衣的都还不曾派人送衣来,到了夜里可咋熬啊。”说着,忍不住将双手凑近炭盆中,却因一日长久的汗水和雪水浸泡,往年的冻疮竟复发了,稍一受热,便是一阵刺痛,他又忍不住“嘶”了一声。
陈忠也脱下了头上所戴兜鍪,卸下两侧鼠毛护耳,随意抹了把脸:“之前天阴了这么些日子,我便觉着不好,料得必有雪至,一早已遣飞毛驰书返幽州,想来很快会有消息。”
李十这才发觉,平日里最爱插科打诨的飞毛不见,原来是叫送信去了,他不免又开始为他担忧:“这么大雪,飞毛也只穿着夹衣,苦了他了。”
飞毛是居庸关丁号烽火台戍守的八个人里年纪最小的,才十七,还是个杂胡混血。他身世也奇,爹是辽人,娘是曾被掳走的汉人边民。听闻他娘死后,他受不得亲爹的打,便逃了。前两年他冒死越关投宋,本要被当奸细处死的,结果他一连说出了十好几个辽兵在关外窥伺大宋的地窝子哨点,立了大功。小郗将军便做主将他保下了,上书回汴京,得了官家许可后,便升他任了承信郎一职,命他戍守长城。
听闻当年他领着宋军去捣辽人的哨点,头一个去的便是他爹所在的骑兵小队,他亲眼看着自己亲爹破口大骂,狼狈不堪被宋军押走,一滴泪都没掉,只是一个人走到茫茫荒野,挖回了他亲娘被丢弃的骸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