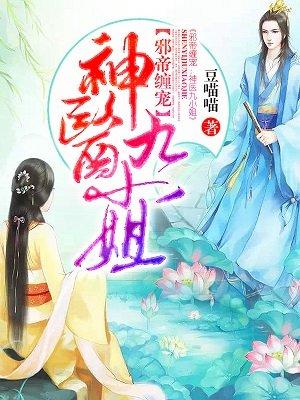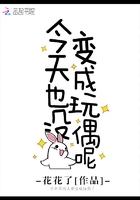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行医在三国作者向晚鲤鱼疯 > 第268章(第1页)
第268章(第1页)
沉甸甸的竹简在掌心之中,从七岁到三十四岁,他和张机聚少离多,唯有笔下学问交在竹简上,一笔一划皆历历可数,刻下的都是这些年的风雨点滴。而今,他交托给青年之手,借他传于后世。董中低头,见昏黄烛火在他眼下掠出细细的影,那双一贯冷静从容的眼,似在怀念什么,轻搭着往下看,看了许久。在他不知所措的片刻,李隐舟慢慢起身,替他整理好书册。“这几年你也去了不少地方吧?”他问,“此前听阿香提过,你都已经娶妻了?”董中望着他弯下的背影,有些不好意思地挠头:“是个候官人家的女子,虽是异乡人,可和我却很合得来。这次特来奔丧,她也是支持的。”候官。李隐舟的视线透过垂下的青衫淡看他一眼,手中动作顿了一顿。董中全没意识到他片刻的讶异,说起媳妇还有些滔滔不绝:“她如今也有了身孕,我已和她议好了,以后也教他从医。有了张机先生的著作启蒙,他一定比我会厉害许多的!”两人收拾一响,董中知他心情低落,有意陪他多说几句热闹话,见已经半夜,也不再叨扰,兴致勃勃抱了书去抄录。送走了董中,李隐舟方从袖中取出陆绩的来信,在豆大的灯火中慢慢展开。……三日后,他送董中踏上回家的路。迎着薄寒的晨风目送董中远去,李隐舟终是将心头一点的疑惑问了出来:“你的孩子,想取什么名?”董中不由地弯起了唇,年少时的冲动与生气都沉淀为眼中一抹温柔的神采。“董奉。”他慢慢地、有些羞怯地道,“不及先生取名之高,我也是昨夜刚拟的,不知好不好。”敬承为奉。董中只是简单地愿自己的血脉能继续走在这条人迹寥寥、艰难苦辛的小路上,将那些曾经前人的心血传延下去。而他也的确做到了,作为建安最后一位出场的神医,董奉将华佗和张机的妙手与仁心传扬至下一个时代,至没有战火的那一天。微风挟着细雨吹散满江薄雾,微澜的江波上照出一长一少比肩而立的身影。李隐舟恍然地想,原来在堂前念书的学子,而今也有了自己的后人。不由想起顾邵院中诵读的少年,想起在陆议臂弯中安然酣睡的小脸,万般回忆涌上心头,在这一刻终觉释然。他望着那无边的江河,轻道:“是个很好的名字。”回城的路上,从碑林擦身而过,他忍不住顿足,隔着绵绵的雨雾,深深地、静静地看他最后一眼。他终于明白了张机的从容——人这一世,不过是在一次次的相逢与送别中走过同一程路,而师傅已经陪他走完了这段本该踽踽独行的人生。现在轮到他,将手递给后来的人。——————————————送走董中,李隐舟亦马不停蹄收拾行囊,准备动身。陆绩的来信他并未声扬,但其中提及了三条极重要的预言,其中陆绩所推演的第二条预言,则是这一年春将在中原爆发的一场大疫。他的三条预言并非是按照年份排布,而是以严重程度第次推进,能排在著名的水淹七军之后,足见这场天降横祸肆虐之盛。经陆绩这样一点醒,李隐舟方后知后觉地回想起这段赫然于历史的弥天大疫,接着便模糊地回忆出曹植那篇著名的《说疫气》。——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不仅贫苦百姓尸横遍野,就连名扬千古的建安七子中仅剩的五人也一齐丧生于这一年。在自然摧枯拉朽的力量面前,人类的兴衰生灭便如草芥般微薄而飘摇,顺可扶摇直上,而逆风时也可瞬间被碾为齑粉。在生命的砝码中,权势、财富乃至于满腹才华、满腔热血都不过是轻易可拂去的一铢添头,仅值一声叹息。李隐舟在这三日内读尽医经钻研防疫、治疫的方剂,为防走漏风声未露丝毫异样,直到登船而去的这一刻才深凝住眉头。沿江北上,两岸苍翠寒山铺如满江浓洒的墨,将春的生气尽锁在泛寒的江波之下。兜头而来的冷风中隐约布散着一种肃杀的气息,凄切风声中偶闻寒鸦一动,便见一双低垂的羽翅掠过惊涛,那白浪中漆黑的一点翻飞片刻,似乎顷刻就要被无边江河吞入沉沉黑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