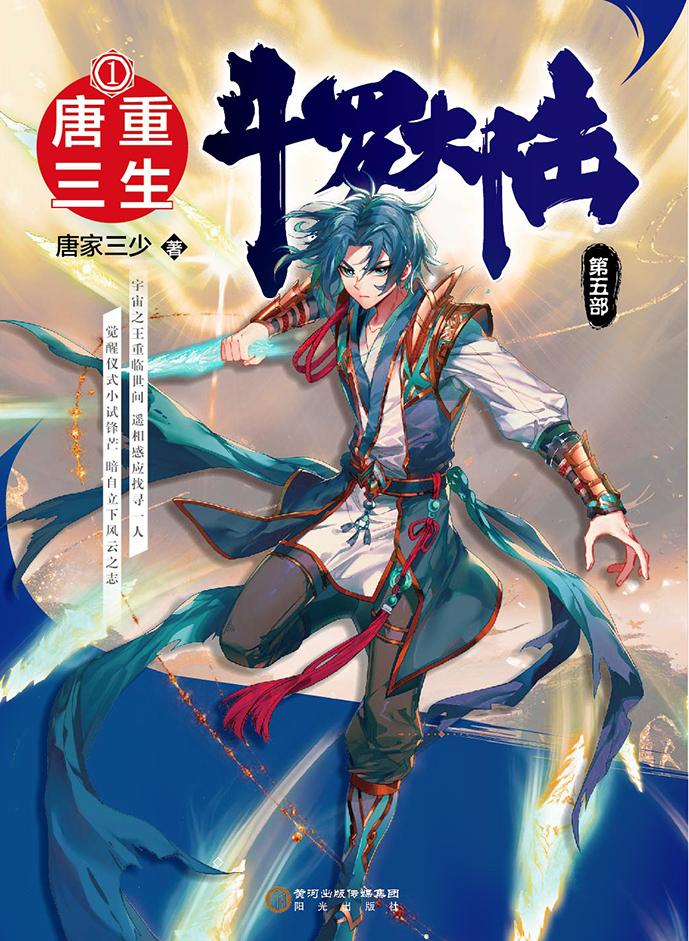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数风流人物 百科 > 第100章(第1页)
第100章(第1页)
他对游时宴转过身,冷漠的脸上浮现出薄薄的红晕,「游时宴,我们一起睡在地上。」
游时宴不想睡在地上,嘟囔道:「可是是我花的钱,凭什么我要睡在地上。」
这也太不公平了。游时宴愤愤不平,不满道:「那你们两个先住这间,我再找一间。正好去外面打听一下拍卖行的事情。」
微尘君从床上变回人身,「义父,你睡床,我可以站着睡觉。」
你们两个就这么不想在一起吗?游时宴很难理解,但好歹有床睡了,凑合道:「那先这样吧。」
烛火摇曳后熄灭,柔和的暖光一寸寸消逝在黑暗里。游时宴不敢脱衣服,和衣而卧刚躺下,就看见微尘君龙眼亮了起来,像两个大灯笼,在夜里无比闪亮。
……忘了龙天生警惕,眼睛会在夜里发光了。
游时宴嘴角一抽,捂住眼睛往被子里钻,假装不知道,但却能明显地感受到微尘君在看自己,锐利的目光反覆打量。
游时宴从床上爬起来,揉了揉头发,吼他,「你再看我试一试,桌上有荷包,你拿着出去玩!」
微尘君听出他发火,致歉道:「义父,可我一直有这个习性。」
他默默把解释的话咽回肚子里,拿着荷包走出去了。
屋里,游时宴躺平休息,脖颈上红线传来一股致命的窒息感,他闷哼道:「微尘君,你快回来!」
微尘君早走远了,沈朝淮十指紧扣,抓住门上的帘子,喘着粗气挣扎道:「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找他回来。」
沈朝淮披上大氅,沿着微尘君的红线去找。游时宴根本没法睡觉,走到窗户上,推开黑夜,看见了微尘君静静地站在楼下。
宁州的夜漫长而热烈,夜市商贩的买卖要吆喝声砸在耳边,像一首终夜不眠的曲调。风呼啸而过,游时宴骤然看到他,微尘君便也静静看回去。
他回望游时宴,神情寂寥而平静,夜色阑珊到了极致。在这零星的烛火里,微尘君却依然不肯移开目光。
那目光不算炽热,也不算多么真挚。只是毫无顾忌丶肆无忌惮地看向游时宴,就像知道游时宴不会过来,也知道游时宴在想什么,是一种平静的守望。
微尘君举起了手中的烛火,千年的韶华像掌心中流逝的云烟一眼,温和而冷淡地照亮了游时宴的脸。
柔柔的风拂在了游时宴的心间,游时宴看见那一缕烛火,烫到了眼底,揉皱了眼底的波澜。
他眼前一热,忽然想到了微尘君最最安静的一次。
那时他攻打虎域,重伤难治。微尘君一言不发,将心头热血喂给自己,紧紧把自己抱在了怀里。
少年人听见微尘君胸膛里一声声剧烈的心跳声,仿若惊涛巨浪。他尝到了一股热泪苦涩的味道,晕染在煞白的唇边。
晕染成一场盛大而无声的告白。
长厌君咽下血,颤着长睫半梦半醒。微尘君抱着他,没有哭也没有笑,柔顺地轻抚着他的长发,反反覆覆,直到心头血彻底流干,直到自己跪在长厌君床边,一声都没有说出。
他没有指望长厌君能活过来,而心头血流尽了,待到长厌君死了,便跟着共赴黄泉。
微尘君分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面前人乖张而桀骜,是天生不懂情爱的灵物,可他真的喜欢。
人间惊鸿客,雪下少年一腔热血,甘愿为自己折腰。所有的爱恨,所有的一切,就全都寓居在无言的静谧中。
正在此时,长厌君突然靠了过来,轻轻贴向了他的额间。
长厌君的额间是一片密布的冷汗,靠向自己的时候不停颤抖,像秋风时凋落的落叶,却仍然带着春天般的烂漫,「小微尘。」
他低声说道,「如果我能活下来,我永远也不会让你出事的。」
微尘君不想听,竟然脑子一热,吻向了他。
长厌君吓了一跳,或许觉得莫名其妙,迷迷糊糊想要推开他的时候,却又听到了微尘君的心跳声。
微尘君的爱,大概嘴上说的总是假的,真正的爱,寓居在心跳中,寓居在长厌君的眼底,寓居在风中雪中还有——少年人永远真挚的心里。
心头血流在二人交缠不清的长发上,嗫嚅湿了一片,正像此刻缠绵多情的红线一样。
游时宴时隔多年恋爱脑差点又犯了,久久无法评平息心绪。微尘君偏偏开了口,淡淡问道:「义父,再见到喜欢的人,有不心动的可能吗?」
他眼睛干涩无比,仍旧不肯放弃看向游时宴,「在我这里,是不可能的。」
游时宴不知道怎么回答,讷讷道:「你说得很对。」
微尘君发现他根本不想思考,执拗道:「我还是云逍的时候,你问过我,拥有喜欢的人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为什么不敢再选我一次?」
游时宴很认真地回答他,「因为上次你把我杀了。」
微尘君冷静地解释着,「义父,我后来自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