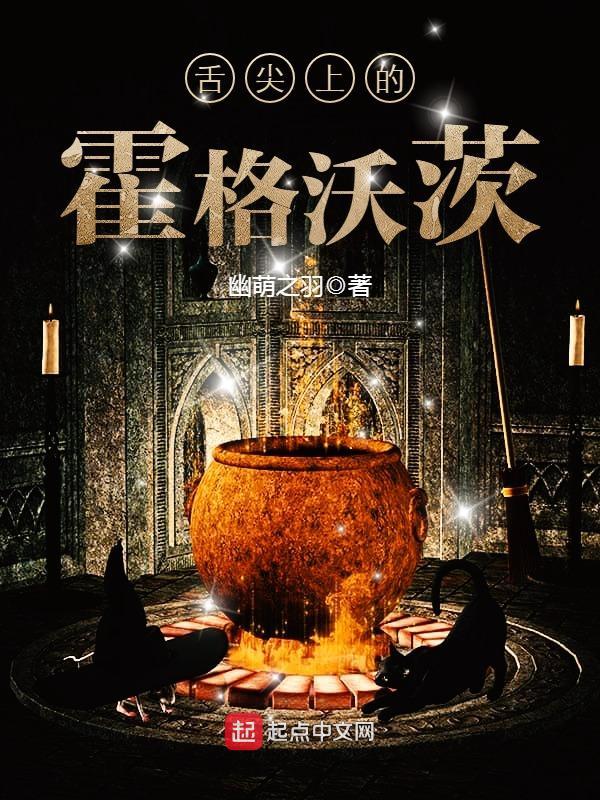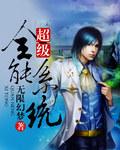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买活御井烹香TXT > 10501060(第3页)
10501060(第3页)
这样,两次学习之后,他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府城,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他来说,却是贯彻知识教戒律的结果。张祭司对此也表示赞赏,再三强调了翻墙进城的后果,以及学习的好处。
“府城之前就很困扰夷人翻墙进城……”
肖美宝附耳对陶珠儿道,“我们是不收进城费的,只是要登记一下而已,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和张老师提了一次,果然有回应……”
而且,可想而知,必定会非常管用。陶珠儿端详着不知不觉,已经聚起数百人的场所,也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她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知识教能办到的事情,很多时候,买活军衙门是办不到的,哪怕是在买活军老地,衙门人手齐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人们不可能会如此虔诚地接受衙门的行为指导,永远不能。
这也能理解吧,这毕竟是极为不同的机构。陶珠儿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她望着张祭司并不高大的身影,咽了咽口水,心跳得有些厉害。她对此简直有些诧异了:要说对牛均田有过一点好感,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小牛算是不错的婚配对象了,他们的条件也比较匹配。可不论是张祭司还是谢阿招,外形不说了,其余条件和她也一点都不合适,她这是怎么了,年纪到了?想成亲了?接连对两个知识教的祭司,都有点异样的反应?
虽然买活军这里,对于女娘的感情道德好像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但大致来说,大众好像也还是推崇从一而终,陶珠儿对于自己‘水性杨花’的天性,也有点儿不安,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都有点魂不守舍,等问答环节结束之后,祭仪进入最重要的考试阶段,她们也跟着领了卷子,胡乱一做,交卷的时候,她都不敢看张祭司的脸,也没有参加后续的评讲卷子活动(考试内容对外援更士来说肯定比较简单),而是托词回了宿舍,独自托腮苦思起来:怎么就特别对知识教的祭司,好像有偏好似的呢?
‘从自身的过去中不断学习’,她算是直接把知识教的教诲给学以致用了,陶珠儿不断回想自己的人生经历,挖掘内心的软弱,苦思冥想了许久,一个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答案,逐渐浮现,连她自己都不觉有些吃惊:
她所喜欢,不,应该说是迷恋的,似乎并不是祭司本人,而是这些祭司所代表的一种状态……一种坚定的、自信的,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去向何处的状态,这种状态让陶珠儿非常的向往,也因此让她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的空虚。
不错,她,陶珠儿,一个极其幸运,也还说得上比较优秀的女更士,内心深处居然似乎缺少一种信仰,让她感到自己缺少了一种内核,感到缺少了一种指导,她似乎居然没有理想更没有追求,好像也很难获取到有益的参考,这一切,造成了她心中那确然存在的空虚!也因此,她才会受到祭司们如此的吸引!
第1053章评价体系缺失
自小生活在深山客户围屋之中,对童年的记忆,大抵是已经多数磨灭了的,只记得迁徙之时,在背篓、箩筐中望着不断颠簸的,细细密密的竹编格漏的光影,至于其余时候,是如何在一个新家乡艰难地站住脚跟,当时的生活有多么困窘……这些陶珠儿的记忆都已经不太清晰了,她似乎并没有生活质量骤然下降的感觉,反而感到从小到大,生活是越过越好的。
隐隐约约,还记得小时候和姐妹们在围屋中无聊且饥饿地玩耍着,偷偷地在亲长家门外埋伏着,觊觎着竹匾上晒着的菜干,如今想来,那菜干简直没有什么可吃的!只有一股青菜特有的苦涩,但在当时,似乎任何能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很珍贵。
反而是搬迁了之后,陶珠儿就没有再饿过肚子了,父母在装饭的时候,也不再是犹豫地打量着孩子们的身量,划算着釜中米饭的数量,谨慎地装出了糙米饭之后,再划算着往里头添一些红薯——再往前的时候,大概红薯都是没有的,农闲时分大家只能吃粥,陶珠儿生下来之后的日子,和以前相比又还算是好过的了,只是这些事情,她当然是一点认知都没有了。
她出身的那个围屋,由于没有参与到客户作乱之中,只是受到牵连,下令分家迁徙,可以选择的迁徙地往往是比较繁华,也比较靠近老家的。很多人不过是从敬州深处,挪移到了沿海而已,陶珠儿一家就没有出广府道,而是在香山县定居下来,做了菜农:香山县距离壕镜很近,自从沿海不再闹倭寇,壕镜开关之后,几处口岸的人越来越多,路也越修越好,这就给周围州县的菜农存在提供了土壤。
他们家里不太种稻谷,大概就种个口粮,余下的地种了各种蔬菜,按照田师傅的吩咐,一年到头都很少有空着的时候。家里的煮饭釜,也不像是从前那么神圣了,以前,只有祖母能打开煮饭釜,给家人分饭,孙子孙女得的总是很少,起码是不够陶珠儿她们吃饱的,孙女就更加如此了。母亲有时候会从自己的碗里偷偷分一点米饭给孩子们,后来想想,她的份量也不多,大概也一样是饿的。
或许是饥饿的记忆太深,到香山县以后,没有多久,他们家对米饭的掌控就放开了,总是一大碗松松的‘二道磨’,那米饭白得发亮——最开始家里大概还吃的是一道磨的糙米,不知道什么时候,顺应村里的风潮,也吃起二道磨来了。那是在老家根本没有品尝过的东西,现在都不限量地让孩子们装,只要能吃完,装几次都可以——或许是受过饿,受过祖母钳制的关系,自从母亲接过掌家的大权,她每顿饭都会多做一点,似乎盆里没有剩饭,她就担心家里有人是没有吃饱的一般。
剩下的米饭,也不会浪费,母亲会撒一些盐巴,加一点辣椒粉,捏成小饭团,就着锅底的余温焙一焙,就温在锅中架着的木格子上,陶珠儿姐妹放学归来,洗洗手可以先拿一个来垫巴肚子……陶珠儿对于饥饿的记忆是很模糊的,打从她开始记事,就一向能吃得很饱,她村子里也没有什么人饿肚皮。现在想想,大概是她没有受过几年饿,所以,就不像是受过饿的兄姐一样,好像心底永远有一股劲儿,让他们停不下脚步。
自古以来,客户人家和广泛居住在南洋的土著相比,有一点让他们很自傲,那就是他们一向非常的勤勉。只要一给他们机会,他们就立刻能发挥出来,从前,这股劲花在了深山老林,和自然的搏斗之中——这也可见岭南有多么棘手了,如此勤奋的客户人家,用了数百年的功夫也没能占据岭南的好耕地,依旧只能在敬州那样的山旮旯里发展,除了南面的气候之外,岭南的土著战斗力也不可小觑。
但是,买活军的搬迁令,让这些客户人家一下就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当然,在最开始,所有人对搬迁令的态度都是消极、负面的,只是不得已地容忍着衙门的倒行逆施而已。可是,一旦适应了香山县的环境,陶家,以及另外几户其余村寨搬来的客户人家,便立刻发现这里的日子有多好过了:
这里的气候,一年两熟到三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田师傅和村长的安排下,米饭可以足足地吃饱,同时,种菜又比种稻子要赚钱得多。只要拿出和山里讨生活一样的劲,一年下来,一家人手里结余个十两银子都不是问题——这还是在不断地添置家什的前提下,倘若家什都置办齐全了,两三年下来,攒出盖个水泥小屋子的钱都有了!?母亲脸上的笑容,变得越来越多了,和父亲一起,他们陀螺一样地忙个不停,每天早起,父亲浇菜,母亲做饭,吃完饭之后,母亲牵着一家人去上扫盲班,扫盲班回来,父亲摘菜,担着去村口和商户结算,回来后做午饭,歇个午觉之后,孩子们大的带小的,都去玩耍了,父母又去地里忙碌,这样到了一天将晚的时候,母亲把今天的扫盲班课程和父亲说一遍,晚上要是还有力气,父亲也会去村里的夜校,在火把的照耀下,认字、做算数,吃早饭的时候,一家人轮流念报给大家听……
只要是汉人,有机会的话,没有不好学的,尤其是传承北方血统的客户人家,更是如此,从前是没有机会,一有机会,家长就非常注重学习,陶珠儿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弟五人从小最害怕的就是考试放榜,如果跌出了班级前十,父母的脸色就不好看。年纪稍长之后,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在村里的几家客户之前,她父母也算是比较开明的,很懂得迎合买地的新政策,对于女儿的培养也很重视。
实际上,村里很多人家,对女儿往往放任自流,绝不会像是对儿子一样,极度关切、苛责。要说不让孩子读书,拘在家里干活,那是没有的,村长可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现,必定软硬兼施地让他们改正——这是可以写到报告里的政绩,又只需要拿捏手心里的村民而已,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他们对女儿的态度,相当的无所谓,会读书就读,不会读书,那就出去做工好了,按时拿钱回来也行,没有本事,赚不到钱,那就等到了年纪,在家里的安排下嫁人,换一笔彩礼也好——在买地这样的环境下,还找不到工作,赚不到工钱,也读不了书的女孩子,差不多也都会听凭家里的摆布,是想不到把彩礼钱留给自己,自己找对象,甚至去争取什么立女户的权力的。
在陶珠儿这一辈,村里的女孩去向就比较繁多了,有些保守的人家,女儿依然是十几岁定亲,甚至偶尔能够听说,有些人家还不到婚龄,就偷偷地去深山里生了孩子,到夫家把日子过起来的也有。
这种事情按道理来说是违法的,两家人都要受累,但村长有时候碍于种种原因也并不深究:没到婚龄就生孩子,仔细追究起来,夫妻两人都要被判刑,孩子也要被抱走去孤儿院,很多人认为这种事损阴功,而且,毫无疑问和这对夫妻的亲眷,从此算是结死仇了,在一些宗族势力仍存,虽然分家了,但没有完全迁徙,依旧有大量亲眷居住在附近的村子,村长也不敢轻举妄动,若是偶有一二这样的事情,也就装聋作哑了,等到现象更普遍一点,那也要进县里商议,看看是不是要借机再大扫荡一次,把妖氛涤荡,宗族的势力再清扫一通。
不过,这样的事情,终究是越来越少见了,陶珠儿同辈的玩伴里,早早定亲,婚书如老式一般,写的是出嫁,彩礼留在女家,嫁妆就几床被子的女娘,大概十个里也就一两个。陶珠儿姐姐就立了女户,她的哥哥弟弟基本也都分家出去,或者去壕镜谋生,或者在香山县内找了个差事,竟无人留在香山村里,算是跳出了农门。她父母种了几年菜,攒本钱也开始做起生意,如今是陶珠儿姐姐帮衬着,将来,甚至可能是姐姐给父母养老,至少在婚事上,是按着招婿的标准来找的。
如此开明的家庭,在客户人家中应该也算是百里挑一,陶珠儿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幸运,哪怕是在家里,她也是最有运气的一个:比弟弟聪明,比兄姐年纪又小,等到开始发育的时候,吃食上就好了,生得很高大。这时候他们也搬迁到了香山县,扫盲班的教育质量也上升了,出山读书也方便了……
陶珠儿在最适合的年纪,条件得到了最关键的改善,才有了如今这令人艳羡的差事,哪怕是一家的亲人,说到这里有时候也有点儿心意难平,她也一向以为自己是很能听得进人言,很惜福也很上进的——如果不上进,她为什么从绍兴跑到楚雄来吃苦呢?
可是,直到她在楚雄见到了知识教的祭仪,她这才明白了自己心中的空虚:她当然知道,她得到的这些机会,这些教育,这些待遇,是多么珍贵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六姐的恩赐,她对六姐的崇敬和忠心,是没有任何人能质疑的。可是……可是这只是知道而已,这种感悟并不入骨。
可能是因为她还在懵懂襁褓之中,就已经受到了恩赐,她不记得也没有体会过,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人生能有多么的悲惨,所以她没有那种急切的,要抓住机会,要享受这种权力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正是她的亲人奋斗不息的动力。
她的父母,睁眼忙到闭眼,闲着半日都感到罪过,因为他们实在是真的饿过肚子的,他们知道劳动无法换得饱腹的感觉,一旦他们发现,劳动可以获得丰厚的报偿,他们就忍不住要去尽量地多做,深怕某一天又失去了这么好的机遇。
陶珠儿的姐姐,她的性格是无比要强的,她极为迫切地要证明自己是足以立得住女户的,性情也坚韧得能承受得住所有的风雨,这无疑是因为她离开围屋的时候,已经快十岁了,已经懂事到把围屋新嫁娘的生活和自己联系起来,意识到那些惨淡、艰难的生活,正是自己的将来。
买活军给予了她摆脱这个未来的机会,她就无时无刻都想要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这份幸运的。包括她的哥哥们也是一样,他们真正受过穷,吃过苦,所以为了把日子一步步变好,永远都有不竭的动力,陶珠儿心想,如果他们来看知识教的祭仪,大概也不会和她一样,产生如此强烈的向往。
她就是知道这些道理,但打从内心,她没有相应的感情,陶珠儿拥有的东西都是在她懂事以前就来的,就好像是天然给予的一样,倘若说要把它拿走,那她当然绝不会答应,并会极度愤怒,但在眼下,无人夺走的此刻,她不会因为自己能吃饱饭,能上学能当吏目就很感动,就不想辜负,她就是没有这种强烈的珍惜感。
那么,促使她来楚雄,谋求晋升的冲动,是什么呢?是对道统的信仰吗?似乎也不是,陶珠儿对政治课所说的道统,当然并不反感,只是她好像也没有这么伟大,自己衣食无忧的时候,还去惦念着别处受苦的人,这必定是要相当有胸怀的英才,才会拥有这么广阔的胸襟,她……她就是个俗人,能力许可的时候她也会想着帮人一把,比如曾经关切楚细柳的行止,但她绝不会为了帮人自己跑到楚雄来。
深夜自思,陶珠儿不得不承认,她来楚雄支援,主要的动力还是在于对成功的向往,人总是要强向上的,也很容易受到旁人的感染,大家都力争上游的时候,你也会想着努力一把,她这一次申请外差,其实主要就是在羊城港看到那么多优秀同仁的拼搏精神,接受了感染——这和受到知识教的感染其实也差不多,只是知识教的祭司,情怀更加崇高纯粹,所以对她的影响也更大而已。
为什么而努力呢?想往上爬?她好像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欲望,想要做好事?似乎也没有这么无私。想要过上一种旁人眼中的模范生活,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或许……或许还真是如此。只是,只是在买地这边,什么样的生活是模范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所以她才会对知识教的祭仪如此感兴趣。陶珠儿对于佛道乃至移鼠会,是完全没有任何好感的,因为她的生活按照这些教派的标准,无疑离经叛道,距离他们所鼓吹的温顺、纯洁相去甚远,知识教倡导的美德,就很符合她的胃口。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生活上诸多细节的关切,对于困难的处理,对于道德的标准等等……虽然是对信徒提出的要求,但好像也提供了一种完成要求后的成就感:加入知识教,就好像多了一个大家庭,有了很多伙伴,你做了对的事情有人赞许,尤其能得到一个崇高的祭司,发自内心的肯定,陶珠儿只要一想到这一点,就油然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她对谢阿招和张祭司那种急切的靠近的冲动,好像就是想通过男女交往来获取这样的肯定,而并不是真正在……在性上受到了他们的吸引。
就算她完全是个新式女娘,想到‘性’这个字,陶珠儿也还是有点羞赧,她坐起身无意识地揪着枕头边角,想道,“肖美宝可能也和我一样,所以才私下拉我去看祭仪吧,我们这些新式的女娘,怎么说呢……别看人数众多,但好像在某个角度来说,也很孤独——不是说身边没有人,而是……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