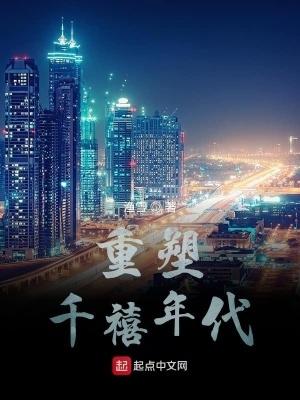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心中下了一场雪 > 第440章(第1页)
第440章(第1页)
对着一大堆还需要继续的工作,陆洋仰头往后靠在了椅背上,心绪久久无法平静。
晚间传来了呼叫,陆洋这个月第一个值班就碰上了紧急情况,本来还埋头正在整理文献和修改论述,接到电话后,急匆匆地披上白大褂就赶了过去。
手术室内各种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安排起来,患者是从心内介入转过来的孩子,在转过来之前,今天刚进行了房间隔缺损介入封堵术。
换过衣服洗过手刚踏进手术室,就已经听到了里面准备间里医生和护士间的对话,焦虑而急躁,争分夺秒的急迫感直接扑面而来。
“林主任大概什么时候到?”
“刚打了电话,暂时赶不过来,分院那边有一台风险很高的急诊夹层,要来也得等一等了,已经在联系其他教授了。”
“陆洋在的,陆洋现在下来了,”手术室的责任护士回过头,看到陆洋已经平举着手进来,立刻露出稍稍松了口气的表情,“来了来了,陆洋来了。”
超声影像和之前的各项检查确认得很仓促,一边穿戴着手术衣和手套,陆洋刚才来得很急,还没有全面地了解患者的情况。
但在匆忙下阅过所有碎片般的信息,陆洋的脑海里也已经大致拼凑起现在的状况。
“现在超声来看,是有一定程度的心包填塞,封堵器脱落这个也有可能是本身边缘组织太薄撑不住导致滑脱。”
心内的医生的语气里明显很是头疼,现在对于一些先心疾病的确已经可以通过微创介入方式进行治疗,可是出现意外情况,能不能及时通过外科治疗,又要怎么面对家属沟通都是需要处理妥善的问题。
陆洋也不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情况了,他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看向跟着自己下来的科室住院医,准备开始手术。
还好是三号术间一切的仪器布置,所有工作习惯都是自己熟悉的。
因为人手不足,楼上只留了两个住院医生在病房忙碌,连带着刚进手术室实习没几次的这批专硕学生,也暂停了常规的值班培训被叫了过来打下手。
陆洋在白天里一直都表现得很安静低调,就像是科室里其他的医生一样,又因为今天跟科室主任之间似乎有着摩擦的暗流在涌动,所以就算是林远琛那句“大师兄”也没有让这几个学生把注意力转移过来。
直到这一刻,看到陆洋作为一个资历不深的主治医生,沉稳地处理着严峻的突发问题,在手术台上,被这个狭窄的空间内所有高年资的护士和其他科室的医生信任着,年轻人们这才明白了这个看上去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科室里许多人却都要叫一声“陆老师”的医生,是有着怎样的能力——林主任暂时赶不过来,但陆洋在也行。
一边忙着手上的工作,一边忍不住多看了站在台边,盯着着经食管超声的主刀一眼,就被陆洋瞪了回来出言警告了。
“专注这种事情还需要我提醒吗?”
声音其实并不严厉,但因为很少见到陆洋这样的严肃,在场的学生们也都震了一下。
陆洋工作的时候延续了林远琛的风格和习惯,没有闲聊,除了跟助手和配合团队必要的确认和沟通之外,一直都保持着沉默,这一台又是急诊紧急手术,也顾不上教学和讲解,整个术间的气氛都有些紧绷。
很多在选择采用微创治疗的考虑里,除了创伤大小和并发症之外,占比较高的出发点就是疤痕问题,陆洋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刀尖做了右腋下弧形切口进胸。
一点一点小心地切割游离,沿着膈神经前缘纵行切开心包悬吊,主动脉和上下腔静脉插管,降温,循环阻断,主动脉根部灌注停跳液和冰屑保护,切开右房,许多工作了多年的心外医生依然需要谨慎地在指导下完成的体外循环建立,陆洋主刀操作起来每一步却都像是训练了无数次的稳当与迅捷。
封堵的失败有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但既然患者已经送到了心外,陆洋能做的就是尽快取出脱落的封堵器,修复心内畸形,让孩子尽快脱离危险。
从右心内将东西夹出来的时候,回到临床,回到手术台,那种自然而然的流畅与熟悉感对陆洋来说,仿佛格外浓烈。
苏教授这时候进入手术室,中途因为知道陆洋已经上台放下心后,所以来时看着倒也不算匆忙。没有接手过主刀的位置,他只是在确认了小患者的情况后,便看着陆洋的操作,接上了助手的位置。
明显是封堵器型号不合适,对于间隔缺损边缘距离的判断也有问题,其实这样的缺损形状和类型做介入是比较冒险的,还好小孩子幸运,没有出现严重的心脏穿孔,也不存在其他复杂的先天性问题。但陆洋没有开口说什么,只是熟练地用缝线和垫片迅速把缺损做了缝合,仔细地检查着瓣膜和连通着心脏心肌供血的血管每一处,完成了补救修复,确认过无残余问题,测试过瓣膜闭合后,开始复温复跳,平安关胸。
“等会儿送到儿童监护室那边的时候,我让小余过去跟一下,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们沟通。”
出于谨慎,最后的表皮缝合,陆洋也没有甩手,不过想到等会儿他也得去见见家属,不禁也有一丝担忧。
苏教授看着,却是不知道第几次发出了带着几分遗憾的感慨:“你虽然这几个月在医院工作的时间少了那么多,但难得完全没有任何退步或是荒废啊,唉呀,早知道那个时候不应该答应远琛的。”
陆洋脸上终于扫开了刚才术中的紧张,露出了几分笑意:“同个科室,您又一直带着我们工作,也教会了我这么多,苏老师这话就见外了啊,都是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