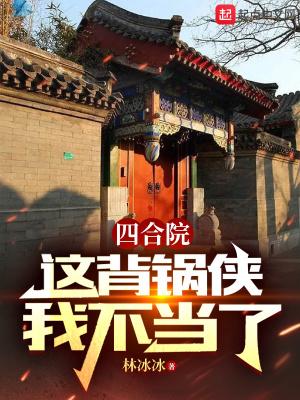永久小说网>买活御井烹香TXT > 10901100(第2页)
10901100(第2页)
至于说,这些人均粮食储备较高的人,他们是不是该死——就如同龚二毛所说的,‘左右都是人命,有什么对错’,在这种极端事态下,对错已经没有意义了,大户不该死,难道饥民就该死了吗?再说,百姓们往往是本分老实的,因为他们没有作恶的条件,而大户则多数都有劣迹,要在道德上找个落脚点,其实也很简单,救灾队员对这种手段,也没有什么抵触心理,他们见过的超乎想象的下限事件,实在是太多了,杀大户远远还排不上号那。
当然,这是不是救灾队该做的事呢?答案也是显然,甚至,龚二毛和黎文都不知道,如果不是救灾队偶然在横渡大河时丢失了传音法螺,好像和家乡也断去了联系,他们自己是否有胆量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在当时,情况就是如此,救灾队突然间和大本营也联系不上了,中原道的局势又很紧急,说好的援助已经运不进来了,在州县这里,还有一批愿意跟随他们的本地有识之士,需要他们的庇护和领导,而此时,来自山阴的饥民日益接近,整个县城都是一副山雨欲来的样子,百姓们惊慌失措,很明显不愿意和大批灾民硬拼,有些甚至已经先下手为强,想着抢一抢,多点粮草,他们好推车先跑了!
这样的危急情况,已经大大超出了救灾队的预计,也不是他们的救灾范围,而救灾队的第一条规矩,就是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救灾,因此,分队队长立刻就提出了撤离计划:按照规定,他们是该立刻组织撤离。到安全地带之后,请示上级,再考量进不进灾区——队员的自身安全,永远是队长的第一考虑。
可队员龚二毛等人,却是于心不忍,他们走是很容易的,可,就如同救灾部的会议上所说,这些依附于他们,一心想要为家乡灾情做点事的当地百姓呢?他们该怎么办?就这样被抛下了吗?还有几乎是注定在饥民冲击下覆灭的县治,这些百姓他们是可以救的,还能努力一二,难道,真就要撒手走了,让他们去承受狂风暴雨的抢掠,损失一切之后,不得不被裹挟进灾民中,让这种损失不断的重复升级吗?
山高皇帝远,没有了传音法螺,身在化外之地,似乎大家都变得任性妄为了起来,当龚二毛胆大包天地质疑起队长的决定时,队内大多数人居然都赞成他的观点——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这些很多本来就来自中原道的汉子,也已经和本地百姓结下了深厚情谊,让他们撒手,情感上的确做不到。
虽然不愿如龚二毛设想的那样,挑头出面,干脆就用买活军救灾队的名义,来组织和融合山阴、中原的灾民,但如果龚二毛真能把义军组织起来,他们也愿意率领一部分灾民分流南下,配合实现龚二毛的构思。
就这样,救灾队发生了第一次分裂——队长阻止不了队员,但仍坚守救灾队秩序,于是便和他们分手,孤身回买,而龚二毛等队员,则组织县里的壮丁,又去和饥民联系,装神弄鬼,借助六姐的权威,唬住了饥民,双方合力,将县里大户的私库、官库的粮食,全都搜出充公,分给百姓食用,这样就保住了地里的青苗和百姓们的性命。同时,又把一部分老弱组织起来,往江北迁徙,这一路上他们的口粮也是要通过大户去‘统筹’的,因此,救灾队员也逐渐分流出去,不断带队南下。
粮食从库里被挖出来了,人员分出去了,青苗保住了,虽然减产,但因为吃粮的人少了,地主都被杀灭了,没了盘剥,那些不愿离开家乡的农户也有了指望,县里也拉起了新的治安互保队伍。
同时,那些能战敢战,可以在很少的军粮供应下,依然维持战斗力的精兵苗子,也被留下来,继续往下一个州县进发——一开始,龚二毛等人绝无带义军去打别的州县的想法,可他们很快发现,这似乎是个不得不做的选择,因为中原道的地主显然没有那么邪恶,储粮是有,但绝没有多到能持续养活一支军队的程度。
事实上,义军的军粮一直紧缺,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七日之积,他们只能不断往前,不断去扩张队伍、分流、杀地主夺私库……这样的前进要走到什么时候,龚二毛和黎文心里都是无数,他们也本能地感到,这种模式是无法永远持续下去的,人员的紧缺近在咫尺:带领百姓南下,这是非救灾队员不能胜任的活,因此,很多队友都是这样孤身领人上路,不能指望他们短时间内返回,基本就等于说,高级干部在一直消耗。
现在,除了龚二毛和黎文之外,也就只有五六个队友了,队伍又在不断扩大,很多岗位离不开他们奔走,如果能成功拿下商都,必然又会分流出一大波百姓,龚二毛现在不知道谁还能组织他们怎么去南面。
摆在眼前的问题太多了,一个个都极为棘手,好像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大家已经不知不觉地缔造出了一点成绩,现在,他们已经是一支颇有规模的义军了,虽然还没有名号,但已经足够引起朝廷的重视。
龚二毛和黎文虽然没有正面谈论此事,还都在低声议论该如何攻打荥阳,但,这天晚上,当他枕着手,看着满天繁星出神时,他心中依然隐隐约约地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龚二毛半点都不诧异,大概是因为他心里也清楚,这样的想法,早已存在了不止一日,只是他以前没有正视。
“其实……就不按六姐的法子办事,或许也是可以的吧……”他想,“按六姐的法子,才需要那么多的吏目,如果……如果按从前的义军法子来做事呢?拿下商都之后,也算是有个基业了,给他们封封官什么的,没准……真能把中原道给经略起来。以战养战,在北方站住脚跟……”
他心中对六姐的崇拜和敬畏,是毋庸置疑的,但身在这个位置上,感受到了一呼百应的滋味,龚二毛心中也不免杂念丛生,给自己寻找着自立门户的理由:“我完全是出于善心,做的好事……只是,和六姐的角度暂且不一样,若继续以六姐手下自居,恐怕会给她带来麻烦。”
“我也是为了我的信念,为了家乡的百姓,我也走在我的正道上……谁知道呢?没准,在这乱世之中,我也会有一番的作为……不敢说胜过六姐,但在史书上,我也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敏朝的皇帝,管不好北方,只能听之任之,为什么不能让有能者来管呢?没准,在我的管理之下,中原道的百姓还能过上好些的日子……”
“啊……如果拿下了商都的话,再用义军来自称,未免也太草率了吧,如果真要封官建制的话,那就要给义军定名了——倒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如果用买活的字号,说不定也真不是六姐乐见,是不是起个旁的名号,看似和买活军毫无关系的,反而好些呢……”
第1092章买地暂且静观其变
“能确认是中原救灾队的人吗?该不会是留下了什么证据吧?”
“证据至少现在看是没有的,当然,也有一些逃出来的百姓说了,这支乱军,一开始以买活军的名号作为招徕,不过这也不能说明什么,这些年来,敏朝凡是有人作乱,就罕有不借用咱们名号的。”
中原道的情况,现在已不是救灾部一人关切了,成为了一个复杂问题,谢双瑶不得不为此在紧张的日程中,挤出时间安排一次小会,并且在会前给大家一定时间,查看刚更新过的各种资料:买地的情报局也并非虚设,在京城已经形成网络,只是囿于消息传递速度这个问题,送来得没那么快罢了。
就是到开会这段时间,也还有很多资料通过有线电报被发过来,这就体现了有线电报的好处,深夜时分它可以连续不断地传达较复杂长篇的消息,要比无线电台的口述好得多。
京城的传言,羊城港这边还是能掌握的,中原道方向的消息少,也不是情报局偷懒,而是那里业已大乱,大家知道的都是邻近省道传来的侧面消息,在中原道救灾队的电台断联之后,就没有别的即时一手通道了。
虽然大家事前都看了简报,但新资料很多都是没看到的,已经被调回外交部做部长的谢向上,就特别从容了,挑选资料细读明显比旁人有章法,对于京城可能的反应,推测起来也是胸有成竹。
“虽说这些年来,有了咱们的帮忙,北方大体局势稳定,但毕竟天候不好是事实,受灾地方,小规模起来作乱的也很多,但凡这是个有些见识的,都会打着咱们的名号。敏朝对此倒也司空见惯了,至于说此次中原道的乱象,咱们救灾队是不是真的掺和其中,或者说干脆就是统领……”
谢向上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笑道,“现如今,敏朝朝堂之上,失地南官还是牢牢把持着大权,北地本就失权,京畿道是特科做主,山阳道、关陇方向,才是北官的根基,中原道出身的高官不多,以如今整个北方的天候,估摸着就算朝堂上收到了详尽消息,也就是装聋作哑——直白说句,其实要打的话,我们取江南就该打起来了,那是真的在挖这些高官的祖坟啊,那时候都没打起来,这一次估计也闹不大。”
他摆出了自己的态度:维持现状的话,双方开战的可能不大,军事不需要特别戒备。要讨论的,该是要不要升级救灾援助力度。去解决现在中原道境内最突出的问题——粮食不够吃,赈济送不到,秩序怎么可能不乱?买地如果要管,那就要准备出兵了。
到这一步,才要去考虑敏朝的反应,否则,如果只是静观其变,敏朝应该也是装聋作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任这支义军自然发展到某个界限,然后自然溃散。
“他们要往北走,那就是去京畿道了,京畿道有火器把守,又是特科经略多年的地盘,兵强马壮,新京营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流民兵问题还是不大的,至于糜烂的灾区,完全可以放弃掉,也的确无余力顾及。我推测敏朝现在的应对就是谨守京畿道。”
“同时行文洛阳,让福王注意防守——甚至,如果再毒辣一点的话,皇帝还可以设法诱惑这支队伍去洛阳,牺牲一个福王,用福王府的私蓄诱惑流民军,使其内乱,这也是常用的计策了。反正,现在皇帝和宗室几近于反目成仇,这样的计策他用出来也不会有什么顾虑的。”
毕竟是浸淫于敏朝官场多年,在京城使团迎来送往,谢向上对敏朝的了解,可谓刻骨,甚至视野还要超过他曾经的教官黄锦。谢双瑶点了点头,“如果我是皇帝,我就会这么做,无非是牺牲一个福王,如果能平息中原道的事态,肯定是划算的。而且这也算是对文官的让步,一举两得,文官也会满意,至少京城压力变小了,而且藩王倒台,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还算是好事呢——”
“所以说,有些事是不能开头的,吃惯了嘴,平时还能克制,一遇事就老想着,明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但也忍不住要去吃,我看,皇帝吃藩王,是有点吃上瘾了。他极大可能会希望把流民军诱惑到洛阳去——反正都是资源暴力再分配嘛,别来分配他的,把福王的盈余一分配,真能让流民军吃饱。”
“这吃饱后,矛盾就陆续来了,凭他什么能人,队伍膨胀得这么快,怎么可能如臂使指,内讧是大概率事件。所谓贿敌以乱,也是多年来剿匪的老办法。”
的确,乱军就是如此,犹如野火,起势的时候,瞧着不可抵挡,可等那点子根基烧没了,散得也很快,天然就不具备扎根能力,就算一开始在活命的压力下,军纪可以胜过传统官军,但生存压力一缓解,个人的小心思一出来,队伍立刻就不好带了。
所以,有时候剿匪的官员,也会利用这种规律,故意让乱军的势力再膨胀一点,等到内部矛盾一积压,再封官许愿,诱惑挑拨,让乱军内部自相残杀起来,这股子劲儿也就泄得差不多了。
同样的,在乱军起势、自相残杀、败落的过程中,也能消耗掉大量人口,让口粮需求下跌,重新回到社会供需平衡线上,很多时候,王朝内部的危机就是这样化解的。
它并不是说某一官员特有能力,而是本身就蕴含了某种规律在内——等什么时候,天灾的负面影响,大到这种内部调节机制也处理不了的时候,那就该改朝换代,用更剧烈的战争来消耗大量人口,重新分配资源,让筛选下来的少量人口,慢慢地在天灾中苟延残喘,等气候重新好起来,再繁衍生息,缔造下一个盛世。
敏朝的灭亡,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在李黄来,不在建州,而是在于这时期的天灾实在是太频繁也太恐怖,没有什么封建王朝能扛得住这个力度,同样的,时势到了这一步,没有李黄来,历史也会缔造出别的黄来,黄来不在关陇,也会出现在中原道。